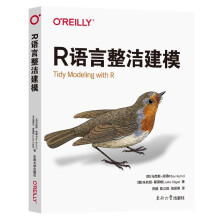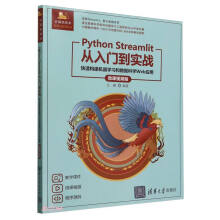格非的《人面桃花》是作家沉潜多年之后奉献给文坛的一部颇具经典意味的优秀长篇小说。古典小说的写作手法和现代派艺术技巧的交相辉映是这部小说突出的文体特征。一方面作者借用荒诞、反讽、幻觉、变形、延宕等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对历史进行解构颠覆。比如小说中的张季元,很显然应该是一位反抗满清统治的革命斗士。但在《人面桃花》中,他却是一个举止委琐的偷情者,他不仅与陆秀米的母亲芸儿有私情,而且对陆秀米本人也充满了强烈的占有欲。这样一种占有欲居然强烈到“没有你,革命何用”的地步。从这句出自张季元日记的表白中,我们可以看到格非对历史明确的反讽与消解意向。另一方面,作者又大量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笔法,将诗、词、歌、赋、铭、记等文体形式有机地切入到文本中,使小说呈现出中国古典美学的含蓄意蕴。比如秀米赠给宝琛一方丝质白帕,上书小诗两句:“未谙梦里风吹灯,可忍醒时雨打窗。”比如秀米出狱后回忆起儿时母亲唱起的歌谣:出了东厢门,就是西厢门。前溪村、后溪村,中间隔着八里坟……等等,真切地反映了主人公当时的感受。
《风雅颂》是一部对当下知识分子精神世界进行严肃思考和无情批判的长篇小说。《风雅颂》这个题目本身便是取自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结《诗经》;小说各卷的标题则以“风”“雅”“颂”,或“风雅之颂”命名;除卷一、卷四、卷八、卷十二,只有总卷名“风雅之颂”外,其余卷次中的若干故事都被作者依据情节内容有选择性地配上了相应的标题,而且,这些标题均是《诗经》中该卷的部分篇名。如卷一总标题为“风”,四个故事情节的题名就都出自于《诗经》中的“风”,依次为“关雎”“汉广”“终风”“萚兮”,其他各卷的命名方式也是如此。因此,从小说的外在形式来看,俨然就是一部《诗经》,但小说所讲述的内容却是对《诗经》的巨大颠覆与反讽。主人公杨科一生研究《诗经》,沉迷于《诗经》,但其所遭遇的一系列离奇荒诞的经历,又分明告诉我们,《诗经》所代表的民族文化精神及传统文人情怀在当下无可挽回的消亡,这正是阎连科在文体上之所以如此设置的隐喻性内涵。
此外,《生死疲劳》中象征、反讽、荒诞手法和明清章回体小说形式的联袂出演;《檀香刑》中赵小甲把爹看成黑豹子,把老婆看成大白蛇等情节描写明显地采用了魔幻手法,而各章都以一段“猫腔·檀香刑”为卷首语,在叙述中又穿插了许多“猫腔”戏文则是对民族形式的有效运用;《受活》不时闪现的寓言色彩和民间耙耧调唱词的采用等等,都是现代主义和古典形式结合的有益探索。
其三,本土化语言叙事策略得到成功运用。
单纯的现代书面语写作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派小说家的审美欲求,而民族的,本土的语言形态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语言资源。
在《受活》中,不仅大量使用方言口语,诸如“受活”“热雪”“处地儿”“儒妮子”“圆全人”“死冷”“满全脸”“脚地”“顶儿”“撒耍娇娇子”等,均是带有明显河南、耙耧地域色彩的方言词语,《人面桃花》的叙述语言则深受古典诗词的影响,具有散文诗般的气韵,古典白话语句的适当插入也为小说增色不少。《生死疲劳》和《檀香刑》依然延续着莫言小说特有的语言狂欢特性,富有胶东地方特色的日常口语和具有极大增殖空间的书面语结合,使莫言的小说看起来就像一场语言的盛宴。而且这些小说中表现出来堪以凝重称之的语言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渗透到了小说的整体叙述流程当中。
总之,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在文体上的创新意识普遍不足,大多数小说家沉湎于“日常叙事”的创作范式当中,希图用这种最传统但却曾经被人们一度搁置的写作方式,产生所谓的“陌生化效应”,对于这一点,文学界的普遍共识是,由于“写什么”已被搁置过久,而“怎样写”却又走向了非理性的极端状态,所以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和采用自然是小说家们走向理性和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样的解释当然不是没有合理性,新时期以来,人们在对小说文体的实验过程中,的确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现实内容的表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的缺憾。因此,重新将创作视野投入到现实当中来,本无可厚非。可问题是,表达对当下现实的理解,却并不就代表着只能以现实主义文体来构建小说文本。内容和表现内容的文体形式其实是两回事,一种内容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一种形式也可以表达多方面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写什么”和“怎样写”并不矛盾。所以,以上的“共识”就未免牵强了。由此,我们不禁怀疑,如此众多的小说家之所以后撤到现实主义文体当中,是否是因为他们在文体探索的道路上感到江郎才尽、力不从心了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并为之揪心的一个问题。因此,能否有效地重新召唤作家们在小说文体创新方面的满腔热情,事实上,已经明显地成为影响长篇小说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有作家能够从我们对这一时期长篇小说文体整体状况的描述与分析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进而尽早寻找到可以摆脱现有写作困境的合理途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