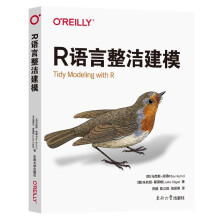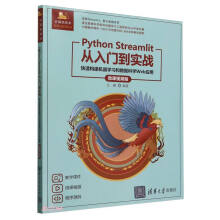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郑语》只写郑桓公姬友于周幽王八年为周司徒时与史伯的一次交谈,议题是面对西周的岌岌可危,姬友怎样才可以“逃死”。两人五问五答,史伯以一千六百多言联系古事与传说纵论时势,断言周王室必衰,而楚、秦、齐、晋将兴,建议姬友暂寄妻儿财富于虢、郐,以后找机会再灭此两国而得其土。姬友于是“东寄孥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后如《史记》所记,“虢、郐果献十邑”③,成就郑国。且不说偌长交谈无法记下,此等背着幽王谋划“逃死”(姬友仍同幽王一起被犬戎所杀)、侵夺他国的言语,怎好留下书面文字?《郑语》何所据而作?史伯言中竟有“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的预言,恰与西周亡年无差,可见是事后诸葛亮把戏的不打自招。
《楚语上》第四章,写蔡声子为救受冤出亡的椒举回楚,对楚令尹子木用四百余言列举王孙启、析公臣、雍子、申公巫臣四位不得已出逃而被晋利用的楚臣,以说服子木;第五章写楚灵王以所筑章华之台为美,伍举(即椒举)一气用六百多言讲论筑台害民危国;第八章写楚灵王阻止白公子张进谏,白公便用四百多言从殷武丁再三请傅说批评自己讲到齐桓、晋文纳谏称霸以讽谏灵公;《楚语下》第一章写楚昭王向观射父问《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之意,观射父以五百多言从上古时代沟通入神的觋巫讲到重氏“司天以属神”、黎氏“司地以属民”以及其后的历史演变;第三章写斗且由于令尹子常当庭问“蓄货聚马”,回到家里便对其弟用四百余言大肆论评令尹的贪婪误国,谓其“必亡”。凡此种种,都不可能是当时史官的如实记录,而是作者根据某些史事、某人言词所作的大力生发和玄想。虽属韦昭之谓“嘉言善语”,却非历史人物之言,多是作者虚拟之语。
《齐语》首章写桓公从鲁国要回管仲,随即问政。管仲对答约六百言,只答“处士、农、工、商若何”之问就一气说了四百八十言,谓四民“勿使杂处”,并细数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的好处和重要性。其实,此等四民所处乃本职使然的自然之势,各代各国大体相同,无须当政者特别强调与关注,为桓公出谋划策的管仲会否就此大发议论姑且不论,只其长言的字数史官就无法记录。可见当非依据齐国“春秋”的实录,而有作者的大力生发与臆想之词。第二、三两章,分别写“乡长复事”和“五属大夫复事”而“桓公亲问”。两章中桓公对乡长和五属大夫各有三问,话并不多,各百余言,奇怪的是这两个百余言几乎一样,只差一两个字,显然不是桓公的说话,而是作者在蓄意作文。不过,上述三章中的造作话语,只是各章的部分内容,并不构成小说,只是蕴涵的小说成分。
《左传》注重记事,人物长话远不及《国语》之多,而数百言一段的长话仍不下十段。七百言上下者就有三段。其中左文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很可能是事先写好的绝交书,可置不论。另外两段则是随时答问之语,似皆变改或生发《国语》之文。其一,左文十八年载,鲁宣公即位不久,莒纪公所黜太子仆“因国人弑纪公,以其宝玉来奔,纳诸宣公”。宣公不但不惩戒,反而“命与之邑”。季文子则使司寇驱之出境。事后,公问其故,季文子让太史克作答,答话除引《周礼》广发道德议论,还讲述远古“八恺…八元”之“十六族”和“四凶”的由来,以及舜助尧选相去凶等“大功”。与之对应的是《鲁语上》第十一章,写的同一件事,却差异甚大:宣公“使仆人以书命季文子”,书被太史里革(即克)调换,将“予之邑”改为“为我流之于夷”。宣公后来追究,太史克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