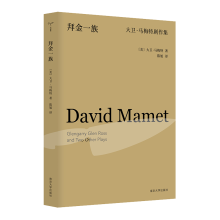《戏曲研究(第92辑)》:
“反讽”作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是在现代西方新批评派将之升格为诗歌基本的语言原则、思想方法和哲学态度,若采取“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这一宽泛把握用来阐释一切作品都是可能且应该的。这里不是要检视或套用反讽理论,而是《圆驾》一出悲喜因素糅合,反讽普遍存在,文本细读与反讽视角是适用的。
判断中国戏曲的悲喜性质,不能看表面情节,应从三个维度考察作品的实质和作者的本意:问题能否现实合理地解决,正面的人物意志实现与否,能否真使读者得到满足感。实则古人早就看出《圆驾》的问题,如三妇评本日:“传奇收场多是结了前案,此独夫妻父女各不相认,另起无限端倪,始以一诏结之,可无强弩之诮。”那么“始以一诏结之”能否真正“团圆”?作者“另起无限端倪”是何意图?细读之下,可以看到柳梦梅、杜宝的心理变化,但根本冲突不能解决,绝非一些学者所谓“喜剧性的戏剧冲突”。前人对此已有揭示,还有几点仍需补充。
1.“(生)岳丈大人拜揖。(外)谁是你岳丈!(生)平章老先生拜揖。(外)谁和你平章?(生笑介)今日梦梅争辩之时,少不的要老平章阁笔。……(外)他骂俺罪人,俺得何罪?(生)你说无罪,便是处分令爱一事,也有三大罪。(外)那三罪?(生)太守纵女游春,一罪。(外)是了。”双方都是心怀不满并立意争辩,而梦梅举出杜宝“一罪”竟是“太守纵女游春”,虽能显出驾驭正统话语的机智与策略,却也自弃了游园惊梦的合法性,反讽中透出一种危险的共识,预示双方都要做出妥协,暂时掩盖冲突以达到团圆假象,这无疑是更深的悲剧。再看两首集唐终场诗:“杜陵寒食草青青,羯鼓声高众乐停。更恨香魂不相遇,春肠遥断牡丹亭。”“千愁万恨过花时,人去人来酒一卮。唱尽新词欢不见,数声啼鸟上花枝。”与“团圆”语境不相侔,对于自由爱情与人性解放来讲,可谓不祥之音。
2.“(外觑旦,作恼介)鬼乜些真个一模二样,大胆,大胆!(作回身跪奏介)臣杜宝谨奏:臣女亡已三年,此女酷似,此必花妖狐媚,假托而成。……愿吾皇向金阶一打,立见妖魔。”回顾《硬拷》一出:“(外)陈先生教的好女学生,成精作怪哩!(末)老相公葫芦提认了罢。(外)先生差矣!此乃妖孽之事,为大臣的,必须奏闻灭除为是。”在古人看来,亡魂作怪或妖魂托名确比重生可信,不能简单把杜宝视为代表礼教的反面人物,他表现的是理性。理性使感性有了现实深度,是人生存的必然要求。题词日:“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邪!”情感世界的逻辑自当如此,果若全不“以理相格”,却也失去现实张力,实则“情”与“理”应构成永恒的互讽。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