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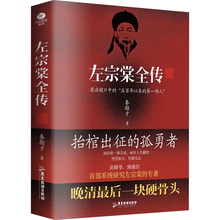
十二世纪,在中国和东突厥斯坦北部,包括现在的蒙古和西伯利亚南方地带这一广大疆域上,居住着许多游牧部落。这些部落大部分是蒙古民族(Mongols),但当时他们都不用这个称谓,“蒙古”这一称呼后来才为他们所采用。
其实,蒙古民族的许多特质,尤其在语言学方面,可以证明其与突厥民族和满洲民族[通古斯(Tunguz)民族群]有密切关系。
那时,蒙古民族祖先的生活,分成“氏族”(Omuk),再由氏族细分为“小氏族”(Yasun,或称“家系”)。几个氏族还可以合并成一个“部落”(Ulus ,或称“小邦”)。
诸如这样的合并形式还有很多。之所以这样合并,有种种原因。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当中产生了卓越的统帅,也有时候因为某一氏族由于各种原因而获得超群的权力和影响,于是就把众多氏族或部落结合在一起,完成政治上的统一。
此外,因为氏族间关系密切,便逐步形成部落联盟。这种情形并不必采取一定的政治形式。这种联盟,只是氏族间基于血统意识或同一方言,以及共同的传统与制度而结缔。由此,一个氏族通过这种形式便能感觉到自己是大部族里的一部分。“氏族”对于“部落”(Ulus)或者“部落联盟”的关系,与各个“成员”、“家族”或“家系”对于“氏族”的关系相同。
蒙古民族的“氏族”和“部落”,分为两个主要集群:草原游牧民、森林狩猎民。这两个集群操着同样的蒙古方言,不同的只是生活方式和文化水准。但这些部落人群心目中却没有感觉到他们是有共同起源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自身是一个整体民族,也没有共同的种族名称。个别氏族(尤其是游牧民族)里为首的通常是一个贵族的家系,依据其身份,他们的领导者有不同的称号,包括:“把阿秃儿”(Bagatur,英雄、勇士)、“薛禅”(Sechen,贤者)、勒格”(Bilge,智慧者)、太子(T‘ai-tsi)、“那颜”(Noyan,统治贵族、官长)等。“部落”或其他“邦”(Ulus)的领导者,则冠以“汗”(Khan,kan,王)或“合罕”(Kagan,皇帝)的尊号。由于与具有高度文化的汉族帝国为邻,一些游牧部族的汗时常从汉人那里接受“王”的封号。总之,游牧的蒙古民族,因为与更文明的民族为邻,或者在十二世纪时占据着从前被后者所居住过的地域而受到不少影响,所以他们之间往往使用外族称号。除汉人使用的“王”和“太子”等称号外,唐兀惕语 (西藏语)“干布”或“札合干布”(Gambo或Djagambo),和突厥语的“的斤”(Tegin)、“必勒格”(Bilge)等称号也在他们中间通用。
由于自身是古老的贵族苗裔,有些氏族易分支成新的“氏族”和“家系”。为了获得独立,这些氏族的“把阿秃儿”和“那颜”开始收揽能够使他们在广袤的草原上占领独立牧地的从臣和家将。蒙古游牧贵族和“把阿秃儿”、“那颜”等豪门氏族的目的有三:一是寻求便利的牧地(蒙古语为Nutuk,突厥语为Yurt),二是众多的属臣和从臣,三是奴隶。这些奴隶可以为他们看管牲口,也可以在贵族帐幕里充作仆役。其实,在“森林民”(Oi-inirgen)中,贵族的地位无足轻重,他们往往扮演着不起眼的角色。森林氏族常常拥立“珊蛮”(Shaman)做其首领,因为他们认为“珊蛮”能够和精灵“对话”,所以“珊蛮”便是氏族和部落领袖,其称号为“别乞”(Beki)。有时草原贵族社会里的成员也使用此称号。
贵族下面的平民蒙古语叫“阿剌惕”(Arat,古代突厥语为Harachu),平民之下就是奴隶,或称“孛斡勒”(Bogul)。
——节选“十二世纪的蒙古民族”
摩诃末的儿子扎兰丁(《元朝秘史》作“扎剌勒丁”)从花剌子模沙那里撤退以后,终于摆脱了蒙古军的追击,甚至还击败了追兵中的一个纵队。他回转到阿富汗的哥疾宁(即《西域记》里的鹤悉那,在今阿富汗喀布尔西南的加兹尼),在那里整编新军,徐图反攻。他是一个果敢而活跃的人物,他不愿意仿效父亲,在没有仔细研究蒙古军及其统帅的卓越特质、没有考察自己军队是否可靠的情况下,扎兰丁便贸然与成吉思汗的军队展开较量。扎兰丁的这种的决断显然是被勇气或一种责任感所鼓舞,但要紧的是,这正是有勇无谋的表现。失吉·忽秃忽奉命进攻扎兰丁,但在八鲁湾一役被扎兰丁击败,几乎溃不成军,被迫率领残余部队狼狈逃回成吉思汗的行营。在整个西进战事中,这场战役是蒙古军所遭遇到的唯一一次严重挫败。而成吉思汗却再次表现出他的宽宏大量,他泰然接受了战败的消息。他说:“失吉·忽秃忽习惯了经常的胜利,还未曾经历过命运的残酷。现在遭遇了这样的挫折,以后应该格外谨慎才好。”(参阅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七章)成吉思汗曾一再体验过命运的残酷,他也经常对将帅们说,命运变幻莫测,所以提醒他们要学习自己所具有的卓越特质——慎重。比如,当成吉思汗听到者别那颜征讨屈出律得手的消息时,便遣使传旨,告诫他不要因胜而骄,因为克烈部的王罕和乃蛮部的太阳汗都是因骄傲而失败的(参阅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五章末)。成吉思汗之所以钟爱失吉·忽秃忽,是因为着他聪明,善于应付新事物,且有坦荡的胸襟及大无畏精神。失吉·忽秃忽的这种勇敢精神,在幼年时代便已显现出来。那时,在严冬的一天,成吉思汗在大雪里迁移营帐时,距营帐不远的地方有一群野鹿经过。失吉·忽秃忽当时只有十五岁,目睹了这件事,便请求营帐总管,在得到许可后,他就到外面去追猎那些由于深雪而不能快跑的野兽。等到日暮驻营时,还不见失吉·忽秃忽回来,这引起了成吉思汗的注意。当他得知孩子迟迟不归的原因时,便恼怒营帐总管,说他不该在大雪天允许一个小孩子独自远离阵营。但就在此时,失吉·忽秃忽回来了,声称自己杀死了三十头野鹿中的二十七头。果然,那些野兽的尸体以后在大雪里被找着了。成吉思汗为此对这个孩子的大胆行动大加赞赏,比以往更喜爱他了。
确认了失吉·忽秃忽的败北程度之后,成吉思汗便采取措施去消除战败的影响。扎兰丁胜利之后,便残酷地杀戮了被俘的蒙古军。他甚至不能杜绝麾下将帅们的争吵,也无法扑灭那些异种混合部队里所燃起的种族猜忌的怒火。这一再暴露了他不过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莽汉,而不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统帅。既然塔里寒此时已落到蒙古军手里,成吉思汗便毫无顾虑地率大军前去讨伐扎兰丁。他路过八鲁湾战场,勘查阵地以后,便埋怨失吉·忽秃忽战场选择不当。扎兰丁在成吉思汗到达以前就早已退却了,成吉思汗一直追击他到申河(Indus,《元朝秘史》译称“申河”,即印度河)河畔。1221年秋,双方在这条河沿岸进行决战。成吉思汗亲自指挥蒙古军,由于扎兰丁不能强行渡河,也不能将其眷属和财物运送到对岸,最后彻底溃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再英武、部下再奋勇杀敌也难逃厄运。在由勇士(把阿秃儿)所编成的蒙古亲卫军——成吉思汗在生死关头方才起用的精锐部队——的攻击下,伊斯兰教军队溃灭。扎兰丁被蒙古骑兵三面围攻,不得不抛下妻妾和子女给胜利者,他自己跃马入申河,一口气游到对岸。据传,成吉思汗当时曾感叹扎兰丁的勇敢行为,并且谕示他的儿子们应该效法这个伊斯兰教斗士。
申河之战是全盘战役过程中伊斯兰教徒军和成吉思汗亲自会战的唯一战事。根据蒙古的传说,扎兰丁算得上是成吉思汗所有敌人中的佼佼者。现在的蒙古人,似乎已经忘记了一切关于花剌子模沙摩诃末那个极不名誉的角色,但当他们对成吉思汗获得光荣胜利的大纛致敬时,一定会忆起扎兰丁,并且认为战败扎兰丁应归功于他们的守护神。
——节选“三大战役与会见长春真人”
对金国的大规模作战,淋漓尽致地显示了成吉思汗的军事天才。历次征战表明,成吉思汗不仅具备军队统帅所拥有的一切资格,也不仅是位有经验有技巧的战术家,还是一个在战场上统兵作战的卓越战略家。他知人善任,经常用巧妙的手法,将归降的敌将委以合适的位置,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才干。他的组织天才也从征集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的部队和迅速组编整个军团上表现出来。将蒙古军的军律推行于这种新编的军队中,大大增加了其战斗力,使蒙古人能够在指挥上更有法度地去指挥新编蒙古部队。
在汉土战役中, 成吉思汗曾被谴责为恐怖、残忍,如千万俘虏被屠杀、全城全州居民惨遭杀戮。但谨慎而细密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些关于成吉思汗及其蒙古民族残暴无常的传说,其实跟历史的真实性毫无关系。与其残忍嗜杀说法相矛盾的是,归顺成吉思汗麾下的许多契丹人、女真人和汉人兵士、将帅及高官们,均受其优待,而这些归顺者也都心甘情愿地为成吉思汗效力。诚然,在若干中原城市中,如果遭到特别顽强的抵抗,或者企图背叛蒙古军,假使成吉思汗认为有必要执行军律时,也会下令屠杀。但成吉思汗从未有过无故的残忍或嗜杀。
北京被占领后,在归附成吉思汗的人当中,有一个前契丹王朝的后裔——耶律楚材。耶律楚材的修养和思想是完全汉化的,他不仅教养极深,也是一个绮丽绝妙的韵文作者。成吉思汗很欣赏耶律楚材的风貌、壮伟身材和他的长髯宏声,于是对耶律楚材说:“辽金世仇,朕为汝雪之。”耶律楚材回答:“臣父祖当委质事之,既为之臣,敢仇君耶?”成吉思汗对他的回答颇为嘉纳,因为他一向主张,臣仆应该效忠其主,即使是他的敌人时也是如此。此后,耶律楚材便陪伴成吉思汗左右。成吉思汗宠任耶律楚材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耶律楚材是一个著名而熟练的占星家。成吉思汗认为他是一个对帝国对自身都有用处的士大夫。这就是成吉思汗对于高度文明的典型态度。当成吉思汗依然是一个草原文盲,从不知道任何科学的观念或者艺术的高级形式时,他常常用最好的方法去对待一切有学问的人,以便积极地利用他们的优越学识为自己更原始的目的服务。
在与异族人的关系处理上, 成吉思汗常常从最初对一个人的理解和后来所做出的正确选择上,去证明他那惊异的天赋。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也是如此,起初是为其占星学上的才识被邀请到宫廷里去,但最后耶律楚材竟成为蒙古帝国里最杰出的政治家。
——“成吉思汗相会耶律楚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