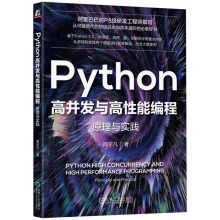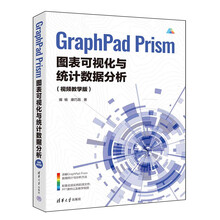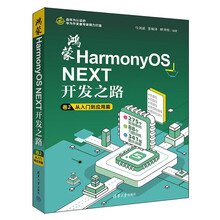《“80后”批评家年选(2014)》:
因其寥若晨星,“80后”少数民族青年作家植根于故土、乡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弥足珍贵。壮族女作家陶丽群的小说《漫山遍野的秋天》中的乡土叙事暗自涌动着一种浑朴粗犷、沉沉实实的生命力。借用作品中对男主人公黄天发的描述,作者也是分外“爱土地,沉沉实实地爱”;分外喜欢看粮食“沉甸甸地挂在那里,那就是日子,沉甸甸的日子”。恰是赖有这种同龄人中极其鲜见的沉实安详的乡土气质,作者连同其笔下人物面对生存的鄙陋、命运的多舛时方能如此难能地忍辱负重,进而赢得“漫山遍野的秋天”的收获。回族作家马金莲的小说《尕师兄》《庄风》《赛麦的院子》《老人与窑》等写的也都是乡村现实、故土情怀,其语言也一样散发出一种植根于民族本土的特有的泥土气息,一种“地之子”般的皈依之情。如果说前者的语言沉重大气,那么,后者的笔触却细腻入微,借用《庄风》中的文字——“看似清风流水一般平常,但关乎每个人安身立命的细微之处”。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民族本土的深爱与忧思,恰是此类题材作品最动人的魅力所在。
较之上述作品的小中见大,蒙古族作家查黑尔·特木日的《巴拉嘎日河边的故事》则显然属于宏大叙事。小说通过一群大学生在巴拉嘎日河畔寻觅、挖掘一部淹埋已久的见证了毡包部落荣辱存亡历史的金字史典的故事,旨在激扬应世世代代守护、传承民族文化遗产这一主题思想。作者不乏史诗追求。
以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壮族作家陆地的《美丽的南方》、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为代表的长篇小说,无疑都充满了“史诗性”;而稍后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张承志、乌热尔图、扎西达娃为代表的中生代作家,其创作也会极其自觉地以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者、代言人的庄严口吻发声。即便所置身的不尽然是一个民族的过去时态,也会情不自禁地将其连通母族的古歌、史诗。自然,这种史诗性造就是圆融贯通的。以此为标杆,《巴拉嘎日河边的故事》未免有机械图解主题、表征史诗之弊;人物塑造也流于平面化,正邪两极对立,缺乏更宽阔、浑厚的人性与民族性的内蕴。
而在另一些“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乡土叙事中,每每可见当代社会日趋多元的价值观念与新历史主义一并谋杀着史诗性的动机。作家们更为注重个人的经历与经验,贴紧当下,随意解构、变形着民族原型、民间传说,自觉非自觉地疏离“史诗”。偶或闪现的史诗意识,也因着个人化叙事的漫漶琐碎而趋于碎片化。
曾经作为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的核心要素、作为审美观照重心的民族性元素,时而也降格为一种“风情”,一种叙事站位,与现代性、先锋性、魔幻性平分秋色,成为小说叙事多重素质之一。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已无心也无力开掘并连通民族庄严的历史、伟大的神祗,却每每沉迷于怪力乱神中。于是,作品中巫师仙娘盛行,民族歌者向隅而泣;而那堪称蒙古族精魂象征的激越高翔的“黑骏马”也终为“流泪的狐狸”喻象所取代。这固然可归因于20世纪90年代以降民族地区日趋混沌多元的魔幻现实的投影,也未尝不是民族自信心愈益式微的表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