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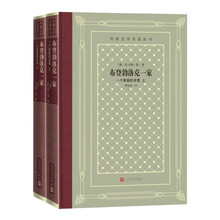

有人的地方,就有《读者》
《读者》杂志创刊三十三年之精华结集【1981—2013】
佳作一网打尽 名家荟萃 余香满口
温情 真挚 纯正 优雅
中国人的心灵读本
是纪念,也是再次出发
海报:
《读者》杂志经典珍藏书系之小品集:从古希腊箴言、英式幽默、日式智慧到中式妙文无所不包,众多领域大师的人生感悟及修行读之令人感佩不已,生命的价值尽在其中。
猫洞
金克木
名人免不了有故事流传,真假难辨。
大科学家牛顿有个传说是:他养了两只猫,一只大,一只小。他为便利猫的出入,在门上开了两个洞,一小,一大。他认为大猫不能进小洞,可不知道小猫能进大洞,开一个洞就够了。这故事是笑学者脱离生活实际,还是笑科学思想方法认死理,不灵活?
牛顿爵士的家世并非贫寒。三百年前,他养猫总有仆人照看吧,何劳他亲身看管?这故事靠不住。
不论真假,这故事里有点道理。开一个猫洞是从人的一方面想,一洞可以两用。若从猫的一方面想呢?一有紧急情况,两猫不能同时进出,势必大的要挤了小的。而且——
大猫:这是我的洞,允许你用,要以我为主。
小猫口头称是,心中不服。
若是各有一洞呢?那就不一样了。
大猫:你看我的洞多么辉煌。我可以让你也利用。
小猫:谢谢。我的玲珑小洞也可以供你用。可是你进得去吗?
双方平等了。各有所得,各霸一方。
故事里的牛顿不可笑。他是从猫一方面考虑的。洞是供猫用的,不是供人用的。对人说,一个洞的效率高。对猫说,两个洞更方便。牛顿讲科学,尊重客观,不由人的主观,考虑事情全面。
无独有偶,中国也有个关于门洞的名人故事。
话说当年齐国宰相晏婴名满天下。据说他曾经当使者到楚国去办外交。楚国人要给他一个“下马威”。因为晏子身材矮小,便在国门之旁开了一个小门,请晏大使从小门进。晏子不肯,说,到什么国进什么门。到狗国才钻狗洞。我来到楚国该进什么门?进大国的大门,还是进小国的小门?楚国人不肯自认小国,只好请他进大门。没开谈判先吃了败仗。
当时只有三个大国:西是秦,东是齐,南是楚。既是外交访问,晏大使必非一个人。代表齐国出访自然有一些随从组成外交使团,骑马乘车,前呼后拥,晏子决不能一个人徒步走来。大使个人的高矮显不出来。而且城墙不是纸糊的,另开一门也不容易。这故事靠不住。
不论真假,这故事里有没有什么道理可谈?
楚人:门是供人走的。大人走大门,小人走小门。门以人为准。
晏子:门是国家的城门。大国的城大,城门也大。小国的城小,门也小。门以国为准。
这又是从两个不同坐标出发看人和门的关系。
事实上,中国历来实行的是楚国式,不是齐国式。贵宾来到,大开中门迎接。来“告帮”的,“求情”的,普通人,都得从侧门出入,先到门房挂号等候。仆役丫环就只能走后门了。
最古的大学叫做“泮宫”。祭孔夫子的“文庙”有三个大门并列。进门便是泮水池,上有三座桥,中间的桥直对“大成殿”。只在本地有人中了状元时才能开正中的大门,由状元走过中间的桥去祭孔。不出状元,就不能开正门,无人走这“状元桥”。门的大小一直是和进出的人的名位身份相连的。不出状元,地方等级就低。
现在的北京大学的大红门是原先的燕京大学修的,仿照“文庙”的格式。不过“状元桥”上走的人不限于状元,中门大开,人人可进了。
人人走桥,未必想到是什么桥。人人知道故事,未必想到里面有什么道理。
1997年第10期
阶级与钢琴
陈丹青
在国中夜访朋友,楼道伸手不见五指,我盲人般趋探蹈步摸索前行,忽然,楼上,或楼上的楼上,传来叮咚琴声。
我就停住,偷听。瞳仁如猫眼,渐渐辨出昏暗中家家户户锅灶碗柜煤气罐自行车等等破旧庄严的轮廓。琴声断续,如牙牙学语。在北京、上海、南京,我几度有幸与巴赫或萧邦的钢琴幽灵在浓黑楼道中相遇。据说,萧邦弹奏时,他的好友喜欢聚在他窗下的花丛中偷听。托尔斯泰写聂赫留朵夫访典狱长不遇,狱长女儿在家弹琴,琴声被门关进关出:即便是书中读“偷听”,也仿佛琴声在耳,极至传神。奇怪,在纽约林肯中心或卡内基音乐厅正襟危坐聆听名家演奏,也不如在这陌生楼道的家常阵地中驻足偷听,魂灵出窍,感动莫名,哪怕偷听的只是小童的初习。
在上海陋巷听到过一回巴赫的帕蒂塔,却是弹得好极,时在盛夏,帕蒂塔一连串清亮的旋律直如风动水流,巴赫在中国有知音。茂名路康乐村,我的小学的后弄堂,还传出比我自藏的所有莫扎特奏鸣曲CD更精彩的弹奏,我一听,暗暗吃惊:是快板乐段,莫扎特的快板总像一个男孩的跳跃奔跑。是掌灯时分,弄内有女人下班的高跟鞋走过,有娘姨开门倒水呼唤小儿,家家传出油锅煎炒与碗盏磕碰的合奏,莫扎特在其间狂奔。我躲在窗下一支烟快要抽完,琴声止息,窗沿传出妇人的咒骂,夹着仿佛筷子敲在木器上的脆响,接着,一个七八岁男孩嗓音嫩嫩地像是女孩,娇声抗辩: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
今日的爹娘们只要凑得起钱,似乎不顾家道的贵贱——不,现在的都市家庭只分贫富而无所谓贵贱了——都愿给孩子买架钢琴弹。三十多年前,沪上的穷街陋巷漆黑楼层听不到巴赫萧邦莫扎特,除非在卢湾区徐汇区原法租界阔人聚居一带,花园洋房,隔着篱笆,春日雨后有哪位“资产阶级”本人或他们的子女在弹琴,那是另一个上海,“阶级”虽已降伏,人还在,钢琴还在,那时,“钢琴”二字即代表出身与阶级。口琴、胡琴、手风琴算什么?“钢琴”是要“钢”做的呀!
英文“钢琴”叫做“Piano”,哪有“钢”的意思?
“文革”起,上海的市井奇谈是淮海路东西两头弄堂里挨户抄家,单是钢琴,抄没一千架!那是我在巨鹿路小菜场听一位弄堂口的赤膊男子亲口宣布的,他拍着肋骨对横在面前排队买菜的人民群众朗声说道:“那么好!我倒想看看伊拉资产阶级从此白相啥?!”翻译过来,即“这下子看看他们怎么玩”。
不久,在淮海路国泰电影院对过一家古董店里,我看见了壮观的景象:大大小小通体锃亮的钢琴堆满店堂,不是那么摆开平放,是上层的钢琴脚戳在下层的琴面上,一架摞一架,有三角大钢琴琴盖卸开,沿墙竖靠着,有琴囊里钢丝钢条给掀得翻翘支棱的,更有在琴壁琴盖上被红卫兵用油漆用刀画的标语口号,店铺职员洗刷收拾,只见倒是抄没资产的人家走出个人来,瞧着更像“资产阶级”:他(她)们终于给整得只剩“阶级”,没有资产了。
忽然,蓝衣女孩的右手掀开临近门口一架钢琴的琴盖,探进左手,大拇指与小手指尖平行张开,熟练地朝那黑色的键盘摁下去。那是她家的,还是别家的钢琴?嗡——钢弦震动,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做“和弦”。我呆住,等她弹下去,但她随即转过青色的资产阶级眼白瞥一眼店堂,飞快合上琴盖——对了,那年月资产阶级的眼神眼色都这么张皇警惕——她闪身逃逸了。店里有大人迎出来,赶开闲人:又一辆卡车轰然转弯满载钢琴,停在店门口。
有谁在公共场所目击自家珍爱的贵重物件给粗暴地扔在那儿吗?人会不由自主寻过去的,只为看那么一眼。我记得蓝衣女孩在钢琴阵地中的眼神,是一种恨意(阶级仇恨?),又是孩童辨认出自己的玩具或宠物似的单纯的惊异(你在这里!)。那一大堆钢琴日后被陆续卖出,易了主了。谁呢?哪个阶级?最便宜的价据说是人民币五十元。
今日沪上的钢琴小天才,那一个个身家既不像无产阶级更不像资产阶级,阶级真的消灭了,除了钢琴。前几年,《东方时空》电视节目曾追踪拍摄孩子们玩儿命练琴,黑压压层层叠叠挤挤挨挨的钢琴仅留得侧身走过的缝隙,像是堆满机床的大车间,店铺给堵得一片昏暗,白天开电灯。我在其间走过来,看过去,时年十三岁。
国泰电影院那年关闭了,不是关闭,所有电影院都用来做大型的批斗会场。临近的“老大昌”“哈尔滨”西式点心店倒是开着,革命人也得吃点心,可这家古董店铺为什么开着,谁来买钢琴?不久传出消息:六十年代钢琴才女顾圣婴与她的母亲兄弟开煤气自杀了。“文革”后一篇回忆文章的作者说是在她寻死前一天亲见她从国泰电影院门口的人丛里走过——此刻,店堂里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深蓝上衣黑皮鞋,也在钢琴缝里走来走去,几次与我擦身而过。我一看,就知道她出身“资产阶级”。凭什么呢?难描难写。我只能说,那时,谁家是山东南下干部,谁家是江浙的民国遗民,谁家世代当工人,谁家的父母是资产阶级,上海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看打扮?资产阶级的子女那时根本不招摇,不打扮,可穿得再朴素也洗不掉资产阶级的阶级烙印。今日上海可瞧不见这样的资产阶级小姑娘了。“资产”不等于“阶级”。现如今,上海小姑娘越穿得“资产阶级”越不像资产阶级,连高级轿车里钻进钻出有资有产的款儿腕儿,也只见资产,不辨“阶级”。那些年,来考音乐学院的纪录片,多是女孩,考上了笑考不上哭,我听着都觉得好极了,想起那位蓝布上衣黑皮鞋的资产阶级女孩,她该早已是一位母亲。节目主持人采访了好几位替孩子进京赶考租房驻扎的父母亲,有西北的农民,有中原城镇的职工,在京城的破烂旮旯里住着,架起炉子披头散发给孩子又做饭又炒菜,孩子呢,脚不及地,高坐在那儿当当地弹——如今判断划分不同“阶级”的,恐怕就是母子之间的那架大钢琴。记得最后一个镜头是琴声停息,小天才扭头冲着妈急。又怎么啦,妈问,孩子娇声吆喝道:
“翻谱呀!”
2005年第4期
人性的墓碑
林达
前不久,我们到美国康涅狄格州去办事,之后绕道去了一个小山村库布鲁克。因为库布鲁克公共墓园中凯灵顿家的家族墓地里,埋葬着一位一百多年前留美的中国人。凯灵顿家族在几十年前就离开了这个山村,不知散落何地,但村人还是把他们家的墓地照顾得非常好。
库布鲁克的公共墓园在一个缓坡上,坡下是一条溪流。在夏日阳光下,读着这个宁静墓园的一个个墓碑,我们注意到,在有些墓碑前,有一面小小的国旗,大部分的墓碑则没有。这小小的国旗插在一块金属牌子后面专门的钮洞里,金属牌本身的铁杆可以插入地面固定。金属标牌的花纹和文字,表明这一纪念组织的名号。当年收留了这位中国人的凯灵顿家的长子,墓碑前也有这样的金属标牌和国旗。
原来,这些有金属标牌和国旗的墓碑下,埋葬着在战争中为国牺牲的人,或者是曾经参军打过仗的人。这是一种荣誉,一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荣誉。
美国人把为国打仗看得非常重。任何一个曾经上过战场、为国家冒过生命危险的人,都可以永远被人称为“英雄”。这种荣誉重到如此地步,可以和生命本身相提并论。若被人指责盗用这种荣誉,就是一种奇耻大辱。十年前,一位美国海军部长由于《新闻周刊》调查他佩戴过专授予英勇作战官兵的一种奖章,质疑他其实没有参加过实战,他为此羞愤得吞枪自杀。可见真正投入战场作战的人,在大家心目中是什么地位。
在库布鲁克山村的墓园里,我逐个看那些金属标牌和国旗,读着墓碑上的文字,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我发现美国北方的墓园和南方的墓园有一个不同。南方墓园也是一样的墓碑,一样有金属标牌,一样插着小旗。可是,北方墓园插的是一色的美国国旗,而南方墓园里,那些牺牲在南北战争中的人,墓碑前插的是南军军旗,也就是北方的联邦政府视之为叛军的军旗。
在南方小镇上,有一个叫做“南军女儿”的组织,一百多年来一直坚持这样的纪念。牺牲的南军将士,当然也是为国捐躯;曾经上过战场的南军士兵,当然也是为了家园才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理当被子孙后代纪念,在他们的墓碑前,理当有一块金属标牌,有一面旗帜,以表彰他们的英雄行为。而他们的墓碑前,不插国旗而插南军军旗,也是理所当然,因为那时候的北方联邦军队,是他们与之流血战斗的敌军。南北之争,是一个半世纪前的政治纷争,而捐躯者,不论南北,一样为后人所纪念。这是一种人之常情。人之常情高于政治纷争。
就是这样简单明了的常识,让美国人不论南北东西,每个小镇的墓园里,都有这样的金属标牌,都有墓碑前的小旗。为国家、为社区冒过生命危险的人,流血牺牲的人,不论是在哪个年代,不论是哪场战争,还有牺牲在和平年代的警察和消防员,在后人心目中,都是英雄,都有特殊的荣誉。
我不由得想,在六十年前的世界大战中,为了不亡国,我们中国人做出了怎样的牺牲?有多少人死在战场上,他们尸骨何在?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为他们插一面小旗,告慰英魂?我们活下来的人,有没有忘记他们?抗日战争中,我国牺牲的少将以上军官超过两百人,在盟军阵营中位居第一。其中,有10%的将军是为战事失利而自杀成仁的,其惨烈程度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有四十四位将军是亲自和日军搏杀而牺牲在战场上的,其英勇悲壮位居世界第一。可如今,我们何处祭将军?
回顾以往半个世纪,我们把政治纷争看得太重了。什么时候,我们也能怀着敬意、谦卑和感激,在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的牌位前,插上一面他们当年在炮火中高举的旗帜以表达纪念,而不管他们曾经是不是政治上的对手?
2011年第9期
弗朗西斯·培根:论美/1
瓦·亚·苏霍姆林斯基:爱,首先意味着献给/3
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节录)/7
亚伦·亚达:走向社会/9
斯蒂芬·茨威格:从罗丹得到的启示/14
武者小路实笃:友谊和个性/18
苏珊娜·布莱特·乔丹:我决不随波逐流/20
马斯洛:低级牢骚·高级牢骚·超级牢骚/22
梁实秋:下棋/25
龙应台:难局/29
余光中:朋友四型/34
杏林子:脱口而出/37
周国平:智慧与人品/39
赫胥黎:科学和艺术/41
古龙:妙论男女/43
梁实秋:旁若无人/47
斯蒂芬·柯维:七大恶/51
金克木:大小猫洞/55
艾尔伯特·哈伯特:把信带给加西亚/58
李敖:好人坏在哪里?/63
王小波 :关于崇高/67
林语堂:脸与法治/71
陈之藩:莫须有与想当然/74
董桥:真难得/77
李方:在古诗里旅行/79
卡尔维诺:经典是什么?/84
林贤治:左拉与左拉们/86
连岳:病/91
董桥:门/93
亦舒:我们活在世上不为求人原谅/96
潘向黎:清白的记录/99
陆文夫:人走与茶凉/103
史蒂文·兰兹伯格:玩什么叫“玩赖”?/106
薛兆丰:经济学能帮多大的忙?/109
苏童:打人有理和自由一种/112
刘元举:风格与耐性/115
李跃:道德的理想高度/117
布丁:听说人家外国/120
崔卫平:野心的权利/122
赵南元:理性与人性/124
冯骥才:选择权是谁的?/128
橡子:没有比信仰更重要的事/131
陈全忠:让规则看守世界/136
陈彤:过好日子也是一种能力/140
赵晓:生命无非记忆/144
毛姆:论见名人/148
谁谁谁:被迫时尚/150
戴维·史密斯:经济学会使你幸福吗?/153
张寿卿:历史题该怎么考?/156
刘索拉:梦想与现实/159
陈丹青:阶级与钢琴/164
龙应台:幸福就是⋯⋯/169
李敬泽:中国精神的关键时刻/172
星竹:付不起的是心态/175
王小波:优越感种种/178
林达:你很重要/182
凸凹:表演的光荣(节选)/187
王周生:有一些感觉正离我们远去/194
谢泳:纸币上的文明/198
王鼎钧:中庸/201
陈丹燕:半爪/203
潘向黎:好的东西,都是不变的/206
葛红兵:高贵的哑巴/212
周涛:猛兽多是懒汉/214
柴静:仁慈的忽视/216
易中天:贵族与流氓/218
徐贲:救命的礼物之链/222
马未都:钱是青春无法驾驭的/225
史铁生:花钱的事/228
许知远:别人的生活/232
王鼎钧:坚守则刚/236
钱理群:黎明的感觉/238
卫撄宁:文化的起源/241
陈祖芬:世界需要天真/244
梁文道:圆明园的道德故事/248
薛巍:美好社会/252
郎咸平:鱼香肉丝与现代汽车/255
保罗·科埃略:人生的四种力量/259
凌河:麦克纳马拉去了哪里?/262
柏杨:老头的悲哀/265
李敖:要成为一个有光彩的人/270
熊培云:自由在高处/274
南怀瑾:禅是什么?/278
林语堂:为什么不去过悠闲的生活呢?/280
李敬泽:老实人和天真汉/282
王鼎钧:我们现代人/287
许锋:做一只刺猬或一条鱼/290
林达:人性的墓碑/293
陈四益:选择/296
老北:左舷是虚构,右舷是事实/298
吴晓波:财富与幸福/301
刘瑜:他们的底线在哪里?/304
程玮:坚守的尊严/309
亦舒:人生一句话可以讲完/311
于坚:生活的魅力:一团乱麻/314
蒋勋:看不见的竞争力/318
倪匡:别人是别人/321
杜尚:人生没有什么事是重要的/323
刀尔登:合理生活/325
林少华:教育,就是留着灯,留着门/327
史铁生:神位·官位·心位/331
蔡澜:一生何求/335
尤今:陀螺与风车/337
木心:鱼丽之宴/340
顾城: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341
聂绀弩:论发脾气/344
冯友兰:论命运/348
王鼎钧:你可能误解乡愁/352
王开岭:一条狗的事业/355
林少华:慢美学/360
张大春:挂在口头上的废话/364
王安忆:型/367
木心:文学回忆录(节选)/370
陈文茜:什么是爱国?/372
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375
杰罗姆·K.杰罗姆:想象中的病人/379
潘采夫:在心里点一盏小灯/383
梁文道:奢华与教养/386
殳俏:一柿情缘/389
刘瑜:爱情饥渴症/392
张炜:安静的角落/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