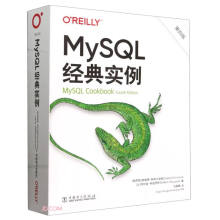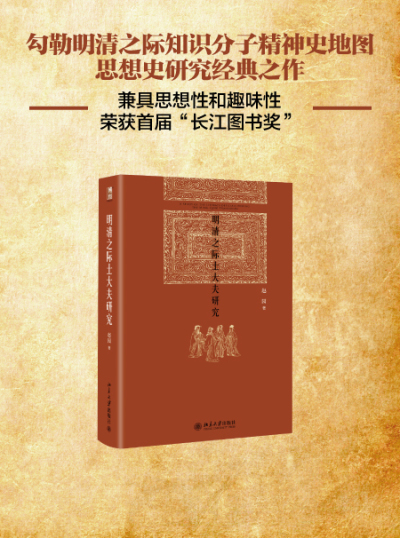赋役阙则刑戮加,衣食匮则寒饿至。则是豪家之命,悬于贫户也。”与黄宗羲的《原君》、《学校》(《明夷待访录》)等,均是应作为思想史的重要材料的。
至于名士或有名士气者,以和光同尘、不别析为洒脱,更有庄禅思想的背景,其文化姿态直接间接地联系于士的平民化、宗教世俗化的进程。宋、元以还儒者、道学与文人、名士,甚至不免有姿态的趋近。邹元标《会语》就有“奴仆就是朋友”、“疲癃皆我同胞”、“渔樵耕牧,均是觉世之人”一类说法(《会语》,《明儒学案》卷二三第536、542页),袁宏道甚至以与“市井屠沽,山鹿野獐,街谈市语,皆同得去,然尚不能合污”为“病”,径说“盖同只见得净不妨秽,魔不碍佛,若合则活将个袁中郎抛人东洋大海,大家浑沦作一团去”(《解脱集》之四《尺牍·朱司理》,《袁宏道集笺校》第508页)。明代尤其明末,世衰而“文人文化”盛。黄宗羲批评吴伟业为园艺家张涟、艺人柳敬亭所撰传,批评王世贞记刻工章筼(《柳敬亭传》、《论文管见》,均见《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即出于儒者对文人文化的批评态度。甚至陈子龙也不满于“近世缀文不别流品”,以致“西蜀富人、阳翟贾客,玄黄所至,缃素斐然”(《应本序》,《陈忠裕全集》卷二五)。“易代”这一大事件对士人生存条件的强行变更,与恢复愿望,更鼓励了文人、名士式的通脱。志在复明的彭士望、魏禧,不惜向“浆博屠沽、下走厮养”搜寻人才;全祖望《祁六公子墓碣铭》记祁彪佳之二子,也说其“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鲒琦亭集》卷一三)。明清之际士人的流品论,作为对上述事态的反应,不能不含义严重。
王夫之对于为时论所称美的“和易”的批评(参看其《搔首问》),可读作其人对士文化的纯洁性、精英品性的关注。而他对“伊尹之耕”、“舜生畎亩之中”一类历史神话的诠释,则提示了经典的误读。他说:“伊尹之耕,傅说之筑,胶鬲之贾,托以隐耳。”(《读通鉴论》卷一〇第375页)而通常的释读于此将“等级”(亦王氏所谓“天秩”)与“所事”混淆了。至于他所说“以躬稼为禹稷之所自兴,则躬稼亦欲张固翕之术也”(《船山全书》第十三册第656页),尤出于对政治的犀利洞察。
流品问题在权力机构中,向有特殊的尖锐性。士流对吏胥的不齿,即影响到明代的政治运作。而与宦官、嬖幸有关的流品问题,更包藏了士人最深切的屈辱之感。宦竖嬖幸,秽乱宫廷,以致陵轹大臣,固无代无之;以画、弈、琴、医、卜等技艺得官爵,也非自明代始。但明代政治的特殊性,尤其所谓“阉祸”,仍然深刻化了士人的有关经验。士人以名器之轻为轻士,为对士的公然的轻蔑;而流品混淆的后果,固在败坏政事,更在破坏等级秩序与败坏士人品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