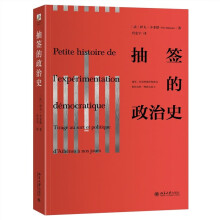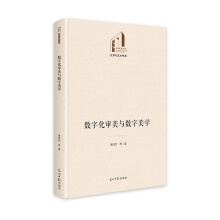危机、风险与福利体制再造
晚近的福利政治研究除了关注研究福利体制的差异性,更加关注其改革动力和自我改造能力。实际上,20世纪7。年代以后,随着石油危机和经济金融危机的呈现,福利制度的压力和可持续性便已成为一个各界所共同关心的问题。80年代以降,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深化、90年代以后的去工业化、老龄化以及女性劳动力的增加、出生率的下降,都加剧了福利国家的财政困境。这些现象催发了关于新社会风险和福利国家调适的研究:国家如何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的经济危机和后工业化社会所生产的新社会风险,社会保护政策如何再造并与之互动演化?福利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制度韧性,这种制度韧性又根植何处?福利体制的兴衰和社会风险的状态密不可分。艾斯平一安德森认为,在工业社会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三种风险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护政策,这包括阶级风险、生命周期风险和代际间风险。三者的共同特征是“收入或所得的不平等”,亦即贫困现象。早期的福利举措所处理的社会压力或风险是有限的,即少数的赤贫者。到20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福利社会进入“充分就业”年代,国家积极干预市场经济以创造就业机会,促使大量劳工阶级脱离了赤贫的处境。因此,社会风险的主要载体就是那些少数没有就业能力的老弱病残人口;而针对那些因为失业致贫的群体,属于小规模和短暂现象,国家通常施以福利供给的增加,尤其是完善社会救助体制。
毫无疑问,至少对于欧洲的福利社会而言,全球化和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带来丁“外生”的社会风险和社会脆弱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通过私有化弱化国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并且相信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或者广义上的再分配能力将因为全球化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生产链条的变化而招致弱化。这种主张并非空穴来风,用Garrett的话来说,“全球化最直接的影响是产生了社会断裂和经济不安全,因为传统的收入和工作机会分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针对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Mishra提出了七个相关的命题:(1)全球化侵蚀了国家追求充分就业及经济成长目标的能力;(2)全球化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导致了后福特主义的劳动形态以及分散化的劳动协商,从而加大了工资与工作条件的不平等;(3)全球化促使国家以减少赤字、负责和减税为首要目标,从而缩减了社会保障和社会支出的规模;(4)全球化弱化了国家的团结纽带以及社会保障的意识形态和理念;(5)全球化改变了劳动力、资本和政府三方的权力平衡关系,损害了三方统合的基础;(6)全球化限制了政策选择的“中间偏左”的立场,致使福利的意识形态出现终结趋势;(7)全球化激发了国族、社群和民主政治的冲突,社会政策将成为首当其冲的议题。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