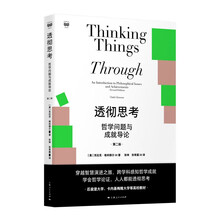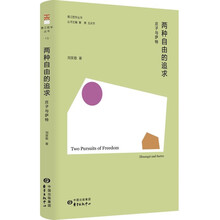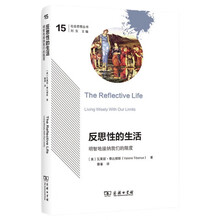就中国形上学建立的进路而言,沈清松指出,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形上学一直是以物理之后的姿态发展,并顾及伦理之后和美感之后。而“中国形上思想自始便以伦理之后(儒家)和意境之后(道家)为主要特质”③。这种以价值为核心的形上学起于对人生的忧患,体现为实践的智慧学,较易切入个人和社会生活。但由于缺乏明显的存有学基础,“无法兼及物理,统纳科学,难以成就一个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基础性的后设言说”④,以致当价值体系发展到高峰以后就难以再有新的发展,并且面临西方文化的冲击显现出创造力衰退的迹象。“其实唯有先致力于存有本身的探索,然后价值体系才不致悬空,价值创造才有无限的客观园地。”⑤台湾新士林哲学家们对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研究大多是力图豁显中国形上思想的存有学基础,而这一豁显又是借助和西方形上学,特别是士林哲学形上学的比较而完成的。这就由理论架构的比较进入到形上学精神的比较。
台湾新士林哲学家对中国形上学和士林哲学形上学的比较,所涉及的方面很多,但其关注的焦点则在于“道本身”和“超越天道”的关系问题,这涉及对中国文化超越形态的把握和理解。诚如我们前面所作的分析,在士林哲学家们看来,诚然在中国哲学的形上学中,强调的是天道、地道、人道的浑然一体的精神,在形上学中并没有对“天道”本身加以专门的理性探讨,从而形成西方形上学式的理性神学,但中国形上中的“道本身”并不封闭在自身内,而是向“超越天道”开放的。中国文化中的天道观是在哲学之外的宗教信仰中的。中国形上学对“道本身”的探讨,是隐然以宗教信仰的天道为基础,但没有将天道纳入形上学之中。这样的形上学架构,在他们看来有利也有弊。其弊端在于,中国文化的主流(儒道)虽然并不阻断和超越天道的关联,但对“道本身”和“人道”的过分强调,使其文化的超越形态局限于内在超越或本性超越中,超性的超越则没有在形上学中彰显,以致在中国形上学中没有为“绝对自有的存有者上帝”和“位格”留有位置,从而也无法在理论上为人生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确立坚实的基础,以至于中国知识界无法抵挡近代以来西方无神论和反形上思潮。其益处则在于,这一超越的天道信仰虽然没有在哲学形上学上得到确立,却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得以保存。这一信仰不是基于抽象的形上学论证,而是基于人的道德实践要求。它强调通过人的道德实践而投靠超越天道。这样的天道观塑造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因而当近代西方的反形上学和反宗教思潮传人中国时,只在知识界发生较大的影响,而对民间信仰影响不大。这乃是因为中国的超越信仰不是基于形上学的论证所致。对此,项退结指出在中国“对有知、有情、有意的上帝失去信心者,往往只限于知识分子;历代最大多数的老百姓始终相信有一个老天爷或天公”①。这就是说,对超越的天的信仰并没有中断,只不过由显形态变为隐形态,而不被思想家所表现而已。
基于对中国形上学的如此了解,台湾新士林哲学家们大多倾向于挖掘中国文化中超越信仰的形上学基础,使之由隐态变为显态。这表现在他们对先秦思想的再诠释上。当然这种诠释是在和士林哲学形上学的比较和会通下进行的。在此诠释的基础上,探寻在中国文化的景观中从形上走向上帝的超越之路。
项退结通过对《书经》永恒哲学的再诠释,来突显儒家哲学的超越基础,他以为道家的非位格的“道”并不能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确立坚实的形上基础。这一非位格的“道”通过易经而融入儒家的形上学,在宋明理学中而至其极,并为当代儒家所继承。这一形上学具有自然主义和泛神论的色彩,这在当代儒家方东美的哲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他看来,泛神论抹杀了神的超越性和存有的等级性,不能为人性和价值确立确然可靠的基础。从《书经》所启示的形上学出发,他对《易经》以后的儒家形上学加以改造,他认为《易经》的“生”字非生命义,乃是化生义。由《易传》所开启的后儒的“一体之仁”形上学乃是基于道家的“通天下一气”的基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