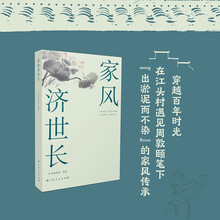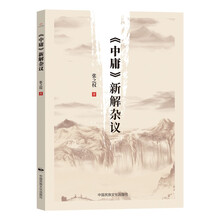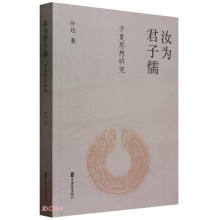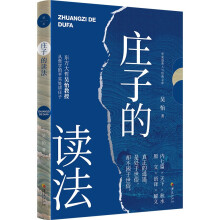《当代中国哲学丛书:先秦儒家哲学知识论体系研究》:
就以身作则而言,“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发布政令非“治”之本、乃“治”之末,而无“本”则不得其“末”;倘若统治者自己无德,其所发布的政令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了,故日:“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如果统治者自己有德,其示范作用正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故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就率先垂范而言,“子路问政,子日:先之劳之。请益。日:无倦”(《论语·子路》)。子路问应当如何执政,孔子回答说,你想让民众做什么、怎么做,你就先这样做给他们看;用你的率先垂范激励他们勤奋劳作、奋发有为。子路请求孔子多说一些,孔子说:永不懈怠。“子张问政。子日: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但必须指出的是,长久以来,存在着简单化地理解孔子所讲“德治”的倾向,即自宋儒依于《礼记·大学》中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把“德治”解释为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宗旨的统治,至今人们大都仍然把孔子讲的“德治”理解为统治者应当在道德品行上为老百姓做出榜样。这样的理解当然不能说错——孔子说过诸如“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等话语,极而言之,甚至说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这里确实有以统治者的个人德性为“德治”之根本的意思。但是,正如前面业已指出的,就“在内圣与外王之间行驶的是直通车吗”这个问题而言,孔子的态度是游移的;所以,把孔子讲的“德治”与“以修身为本”等同起来是片面的,他讲的“德治”还包括在最崇高的人格德性与最伟大的社会功业“之间”的事情。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日: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统治者以庄重之心对待老百姓的事情,老百姓才会敬重你;统治者孝敬父母爱怜子女,老百姓才会尽心竭力地对待国家的事情;统治者把有才德的人提拔上来,给予弱势群体以特别的帮助,以提高他们自强的能力,老百姓才会努力上进、奋发有为。孔子特别强调“举善”的重要性,“哀公问日: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日: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把那些正直的人提拔起来,老百姓就高兴了;把那些邪曲的人提拔起来,老百姓就会不高兴。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日:“知人。”樊迟未达。子日:“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日,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日:“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举善”是“德治”的内在要求,是“仁”之“政”的基本举措,所谓仁者爱人,首先就表现在“用人”这件事情上,要让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就要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而后那些邪曲的人才会逐渐地变得正直起来。所以,“仁”之为“爱人”不仅属于情感表达层面的事情,也属于理性认知层面的事情,它内在地要求着“知人”,是谓仁智统一;进而,“仁”之为“爱人”不仅仅属于心理层面的事情,更属于政策层面的事情,它内在地要求着“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子贡问政。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日:去兵。子贡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日: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引文中的“民信之”,意思是取信于民,老百姓对统治者没有信心,就不可能自立自强。在孔子看来,政治的基本事情有三项,要有足够的粮食以供生存,要有足够的军备以供自卫,而前提是统治者要取信于民。“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乃取信于民之根本,而后可以足食、足兵,这些都是统治者所当“为”,不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所能“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