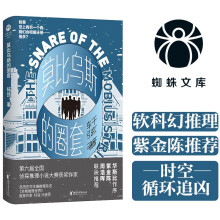第一章 序论<br /> “寂”与我国国民的审美意识 / “寂”的审美内容研究的缺乏 / 缺乏的原因 / 历史研究的见地 / 美及艺术中的日本性格(精神性) / 日本的独特审美概念的美学研究 / “寂”的研究中的美学方法之一:语义及用例的检讨 / “寂”的研究中的美学方法之二:对俳谐的美学考察 / “寂”的研究中的美学方法之三:对俳论中的美学问题的考察与“幽玄”“物哀”等概念一样,“寂”(さび)这个词显然也是一个审美概念或美的形态。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特殊形态的美,在日本国民的某个时代,或在某种艺术样式、某种艺术的生活方式中,例如俳谐①俳谐(はいかい):原文为汉语词,指谐谑取笑的言辞。在日语中,作为一个重要的文体概念,指:一、“俳谐歌”的略称,即带有滑稽谐谑意味的和歌;二、“俳谐连歌”(又称“连句”)的略称,指具有滑稽、通俗趣味的连歌;三、日本近世(江户时代)以降,是发句(连歌中的首句,有“五七五”共十七个音节,近代以后称为“俳句”)和“连句”的总称。在本书中,“俳谐”主要是指俳句,有时也指俳谐连歌(连句)。不少情况下,作者将“俳句”与“俳谐”二词并用或混用。、茶道等之类的所谓“风雅之道”中表现出来。有时候它不仅仅作为一种理念,而且在艺术与生活当中被某种程度上地具体化,在享受艺术生活的国民的审美体验中,被把握、被欣赏。而且,这种特殊的艺术生活中所包含的某种民众性,以及某一时代特别流行与发达的文化潮流,都使得人们对于这种美的感受性与趣味性得以普及。这一事实恐怕也是众所公认的。另一方面,“寂”这个概念所表示的特殊形态的美,也天然地与日本及东洋的民族趣味相投合,对于这种特殊之美的感受乃至欣赏趣味,造就了我国国民审美意识的重要方面,这一事实也是确凿无疑的。<br /> 不仅如此,据我所知,对于“寂”这一审美概念的理论的检讨,较之对“幽玄”、“物哀”等其他审美概念的理论探讨则要贫乏得多。即使说以前从未有过这一类的尝试,也不过分。另一方面,日本传统的审美概念都表示着极度非合理的内容,而一直以来在日本并没有所谓“美学的研究”这样的学问。因而,对“寂”的特别的考察和研究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对于“幽玄”、“物哀”等概念的研究尽管也嫌贫乏,但毕竟在中世时代的歌学书、近世的本居宣长等人的著作当中,都做过某种程度的美学意义上的考察。在俳谐方面,“寂”作为一种“艺术”中的根本问题,以蕉门①蕉门:指江户时代以松尾芭蕉为中心、由芭蕉弟子及追随者形成的俳谐流派,其风格被称为“蕉风”,是俳谐的“正风”和主流。的各务支考等人为中心,很多俳人②俳人:从事俳谐(俳句)创作的人。在其俳论③俳论:对俳谐或俳句所在的鉴赏与评论,成书者又称“俳论书”。中都有过种种议论。然而在众多的俳论当中,对“蕉风俳谐”的“寂”只是在理念的意义上加以强调,直接对其特殊的审美内涵加以理论反省和讨论的却非常稀见。除了那些模棱两可的只言片语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br /> 这种情况的产生,有其种种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在我看来,其中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基于以下的缘由:“寂”这个概念,在芭蕉及其门人作为俳谐的审美理念加以强调时,赋予了太多高深、广泛、复杂的内容,其中的奥妙真谛,除了芭蕉这样的登堂入奥的人之外,毕竟是很难把握的,也可以说是完全不可言说的。不过,如果把“寂”单纯地限定在“闲寂”这个意义上的话,这倒是非常简单明了,但那样一来,除了这个字本身的意味之外,并没有其他意味了。于是,“寂”这个词,就在明与暗两极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意思非常明了,以至于无须加以任何积极的说明;另一方面,它又是极不明了的,以至于在单纯的、消极的否定说明之外,不需要再加什么积极的解释。连写了很多俳论书、在这个问题上极尽饶舌的各务支考那样的人,尽管频频使用“寂”这个词,却对其本身的内容几乎不加任何说明和分析。而向井去来也在他的《花实集》中说过这样的话:“像‘寂’(さび)、‘位’(くらい)、‘细柔’(ほそみ)①细柔:俳论的重要概念之一,日文写作“ほそみ”或“細み”。、‘枝折’(しをり)②枝折:俳论的重要概念之一,日文假名写作“しをり”或“しほり”或“しおり”,蕉风俳谐的审美理念之一,指一种如柔枝一般的委曲婉转的风姿。这样的词,是用言语笔头难以说清的。”他只是举出了他的老师芭蕉对相关俳句加以品评的例子。(在《去来抄》中,他也说过类似的话:“总之,‘寂’‘位’‘细柔’‘枝折’等,只能以心传心。”)<br /> 到了现代,与“幽玄”“物哀”等概念同时,“寂”这个概念也常被日本文学研究者提出来,并加以解释和讨论。对这些解释和讨论加以概观就会发现,在很多场合下,“寂”“幽玄”“物哀”这些概念,是被过分紧密地在某种语境中结合在一起,毋宁说人们都在寻求和阐明这些概念共通的审美本质。例如,在谈到这些概念的时候,人们往往解释为,这是同一审美本质的三个侧面的历史显现;或者又解释为,“寂”的概念是中世时代的“幽玄”概念在近世俳谐中的演变。当然,我并不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从文学史和精神史的立场上看,我们不能满足于把历史的现象仅仅作个别的孤立的解释,而是要尽可能从民族的精神本质的不同表现这一角度加以考察,并确认它的统一性,这也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特别是最近在精神史和思想史研究方面,以西洋的精神与思想为参照,更倾向于强调东洋的或者日本的特性,这是当下时代流行的学术思潮。在这种背景下,仅仅对日本国民的审美意识和艺术思想中的个别的、孤立的现象与问题加以研究,往往不能充分满足这一要求,于是便急切地寻求贯穿于所有个别现象中的所谓“日本的”统一性原理。这种做法,倒也是可以理解的。<br /> 对“幽玄”“物哀”“寂”等诸概念进行研究的时候,比起对这些概念所包含的种种审美的本质特性一一加以考察研究,较为便利的还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混合体,把这些日本式的审美范畴作为一个统一的问题加以处理,在美和艺术领域中阐发所谓“日本的”东西,以弘扬所谓“日本精神”。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存在于美与艺术当中的“日本的东西”的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它所包含的一种深刻的精神性,这一点恐怕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的。我们在这里无法对这种精神性详加探讨,但可以说,这个意义上的精神性的深度,并非只限于美和艺术领域,它与道德、与宗教也有着深刻的关系,而其真正的源头毋宁说本来就发端于非审美的、超艺术的领域。在我国,之所以能够把各种艺术从单纯的“术”发展到“道”的境界,无疑都有赖于这一精神源泉。而要对这个意义上的精神性的特色,作为“日本的东西”加以强调的话,就如同把和歌、俳谐、绘画等其他各种艺术领域都在终极上归结于精神性的“道”一样。这样一来,所谓“幽玄”“物哀”“寂”等从各种艺术的母胎乃至根基上各自发展起来并形成的特殊的审美范畴,便被抹掉了各自的特色,而被统一到一个共通的“日本式”的审美意识或趣味本质上去了。<br />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