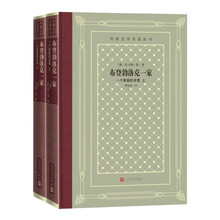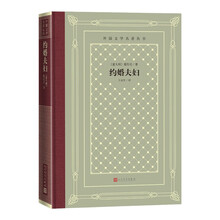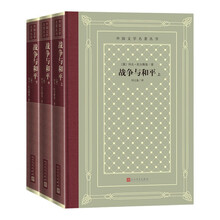沙汀:与土地血肉牵连的作家(序)
我之认识钟庆成(细数起来时间不短了),其缘来自沙汀。沙老与自己故乡四川的那份感情是十分动人的。这足以涵盖他的一生,包括他的创作与川西北乡镇的拉扯不断的关系,他和成都盐道街省一师同班同学艾芜的终生友谊,他多次因命运而远离故里,如1929年的赴上海、1938年的赴延安、1953年和1978年的两次赴北京,但最终一次又一次地魂牵梦萦般回到四川。连同他的个性、爱好、脾性,在在都与故乡有着血缘般的牵连。他最后一次由北京回归四川时已双目失明,却毅然决然离开北京木樨地的部长住宅,返成都定居,从此再也没有挪动过一步。那时四川作协派出协助沙老晚年工作而与之朝夕共处的秘书,即钟庆成也。
南国的花城出版社出了个好选题,要给现代文学家们另出别集。遴选的作家都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者,书却不求其堂皇,不像文集、全集那般正襟危坐,只是一本头的,故名“大家小集”。他们找钟庆成编沙汀,可称独具只眼,是很相宜的。不料庆成竟指定我来写序言,让我无可推托。或许在我的心里,暗自想的正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重温一下沙汀,再读那些像醇酒酽茶一样的小说吧,于是勉力应承下来了。
沙汀中青年时期的写作是他的人生高峰,正当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繁盛、传播的年代。风云际会,他赶上了。那又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坐了主位,中国小说从写故事转为写人物的时代,他不偏不倚也迎上了,并且在强手如林的众多作家中脱颖而出。每个人的写作都离不开他的文化环境、历史语境,沙老的作品在离开了那个诞生它们的环境之后,到现在还有没有当下的读者来读,还有没有一些“永久”的东西能存留在文学史中,这成了一个问题。“大家小集”要回答的也是这个问题。而根据我这几年的编书经验,中国现代文学在“经典化”的过程中接受历史的检验,除去理应被逐步淘汰的东西,从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文学当中初选出二十位到五十位作家的作品供读者鉴赏阅读,似乎还是可行的。这方面的标志之一,就是这种选集还卖得动,有市场,有人理会。我自己近年来编过老舍的、施蛰存的、丰子恺的、冯至的书,今年曾参与审订小学生老舍读本和小学生汪曾祺读本,都给我如此的印象。
那么,沙汀怎样?
应当说,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个历史地审视沙汀的良好时机和立场。我们曾经有过“独尊现实主义”的时期,所幸已然过去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原来非正宗的主观抒情性的作品,曾遭受“腐朽资本主义产物”恶名的现代派或仿现代派的作品大行其道,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我们没有让历史循环,走回头路,再产生一个“独尊现代主义”的时代。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独尊”什么都是不可靠的,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首先毁坏的即是被“独尊”的事物本身。即使它本来还是个历史的中间物、过渡物,还有它长期存在的价值,却也会在“独尊”的大河激荡中提前被击穿至百孔千疮。现在我们可以具备一副比较冷静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流派、社团、文体、创作方法合成的“多元共生”的局面。在这样的格局中,沙汀不会没顶,他有力量浮出水面,表现出一个乡土的、喜剧的、文学语言鲜明的、风格独异的左翼现实主义作家的当行本色。这是:
第一,沙汀在左翼现实主义作家当中的特殊性,在于他对社会形象的捕捉、融化、提炼,其中经由一定的分析理解,又还原为生活的典型化之后的具象。这类作家在文学史上被推为“社会剖析派”,是以茅盾为首,并加上沙汀、吴组缃,这样一些左翼青年作家构成的。茅盾能写上海、江浙市镇,吴组缃写安徽乡土,沙汀写四川乡场,各有各的特点,不相混同。形象思维掺入理性思维如果得法,像这几位,自然能够加大艺术作品的开掘深度、力度。我们不能否定艺术的概念化来自那些粗劣的理性教条干扰,同样不能否定如调适得当,就会给艺术带来特殊的色彩与品味。我们看沙汀的川西北乡镇叙事,他对家乡的人物故事场景真是透骨般的熟知,加上他对中国底层乡土社会权力结构的深度剖析,对这种“乡土权力”的想象和表现,在中国还有谁能超得过他呢?比如这种“权力”的强暴性,无法无天到无所顾忌的程度,像《丁跛公》、《代理县长》里“瘦狗还要炼它三斤油”的横征暴敛;“权力”的欺骗性如《防空》式中国官场的敷衍成性,扩大为欺上瞒下、走官场形式等;“权力”斗争中大众的缺席是因人民的权益已经无处申诉、被无视收缩为零,于是只见“权力”和“权力”之间的倾轧、内讧,如沙汀最擅长描写的乡土基层势力内斗的出色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杰出的长篇《淘金记》。这是沙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贡献。如果细心阅读几部当下河南籍作家的小说,看他们着力描写一个村庄为争夺“村长”或某个芝麻绿豆般的位置而发生的生死角逐,就可以知道沙汀仍在,沙汀的乡土社会分析小说还可读。所以,最近刚出版的一本文学史评价说,沙汀“成功地把两位前辈作家开创的小说写作传统——鲁迅的乡土写实小说与茅盾的社会分析小说——消化并整合为自己的素养,而正是这二者的结合使他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社会分析的观点去深入开掘自己丰厚的乡土经验,胜任愉快地用小说完成了对抗战时期中国农村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分析,描绘出了它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与纷繁复杂的全景”。〔严家炎先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卷)》〕
第二,他是杰出的地方风俗史记述者。此为二十世纪中国乡土叙事不可忽视的特点,而且与作家们分别归属何种政治文化的派别无涉。我们见到“五四”乡土小说中的鲁迅、王鲁彦、台静农、许杰、蹇先艾、彭家煌笔下的浙东、安徽、贵州、湖南乡间的风俗如画;见到京派的废名、沈从文充满诗意的湖北黄梅和湘西沅水流域的风俗长幅;而左翼的沙汀确能精心描绘他的四川乡镇的偏僻、荒凉又充满戏剧张力的景象。如本书开篇《某镇纪事》所写涪江流域小镇的琐碎日常生活,各色的茶馆、客店、食铺,夜晚的“打围鼓”、“讲圣谕”(说书),物产之外更加“出产”的土匪、哥老会、地方财主势力间的江湖事迹。静态风俗外更重要的兼有动态风俗色彩的乡民生活方式描写,如中国南北都有的“吃讲茶”,在沙汀写来就极富川味的麻辣感(沉闷生活中突破性的高亢斗嘴,如川戏之高腔);南北方也同样写保甲长一类人物,可沙汀塑造的联保主任们是多么地狂妄,多么地横行乡里,个个都仿佛是山高皇帝远的土皇帝一般。这是他提供的风俗性四川人物画廊。
第三,他是个对于社会世态,执暴露型文体而又懂得喜剧趣味的讽刺家。这很大一部分得力于他是一个天性偏于幽默玩笑的川人。中国自来有暴露的传统,鲁迅命名的近代“谴责小说”,“谴责”二字就是“暴露”的意思。如果只是为暴露而暴露,缺乏了“公心”,就会堕落成“黑幕”。而左翼的具有政治理想的暴露型讽刺是富有“公心”的,在上世纪30年代以后,与代表市民暴露、市民幽默的老舍、林语堂有了区别,但都具积极意义。左翼讽刺的社会力度、深度在沙汀身上体现了出来,而它的“软肋”,即缺少喜剧的轻松的笑,不分对象地重炮般予以批判往往显出讽刺的僵硬来,在沙汀这里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沙汀对暴露分门别类,“鞭挞”也分清恶人和庸人,比如《兽道》对兽兵强奸月子里妇女的恶行给予痛斥,《龚老法团》却是开着玩笑讲述着在政治角斗场边缘稀里糊涂存在的老派官僚龚春官。他的暴露黑暗至极的小说《在祠堂里》,小军阀将活人钉入棺材,环境场面的气氛传诉却含诗意。《一个秋天晚上》更是一篇出名的将欺辱下等妓女的故事演化成善良人性发现的故事,其间充溢着一丝温情也不缺少诗性。《艺术干事》在沙汀小说里算得是另类,在暴露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的空隙,夹入对无机心的青春活力的礼赞。而因篇幅较长未能选入本书的《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是善意地讽刺抗战文化消费的作品,从头至尾让人苦笑、讪笑不止。这样,沙汀就创造出讽刺的各种品类,将暴露与政治评判结合的,与轻松玩笑、与诗意、与抒情联姻的,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大大提升了中国讽刺艺术的内涵和水平。
第四,显示了民间口语经提炼而文学化的成功。左翼文学从它建立的时候起,就一直致力于“文艺大众化”,其中就包括“大众语”的讨论。上世纪30年代的青年作家沙汀们都既尊重“五四”建立现代白话文学的功绩,也明白“五四”后白话过度欧化、脱离大众的缺陷。结论是要吸收活人的口语,来调适欧化的白话。朱自清先生甚至赞美李健吾纯用北京口语写的第一人称自述小说。到了老舍、沈从文、张天翼、沙汀、穆时英等陆续出来,文学白话便如同上了一层楼,一直通向当代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这种可称典范现代白话文的境地。这中间,沙汀的文字也值得一提,主要是敢用地方口语(易被外地方的人所理解的)融入普通白话,以造成白话贴近社会的生动性。对话如用口语,像《在其香居茶馆里》在兵役中吃亏的“土劣”邢幺吵吵上来第一句话“看阳沟里还把船翻了么”,就活现他不忌生冷的性格。联保主任方治国辩解的声口是“我一定要抓他的人做啥呢?难道‘委员长’会赏我个状元当么?没讲的话,这街上的事,一向糊得圆我总是糊的”,以退为进,阴险狡黠。方言“糊得圆”没有谁看不懂。这是充分发扬白话刻画人物的雕镂性。叙述的文字可以推动情节,可以评价人物,如说这个联保主任,“人们一般都叫他做软硬人,碰见老虎他是绵羊,如果对方是绵羊呢,他又变成了老虎了”。“软硬人”的意思一说也就明白。这种沙汀式的文字,简约、新鲜、活生生的,非常富有表现力。
第五,他完善了、创新了新文学的文体。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在沙汀的手里成了人物刻画圆熟、结构充满戏剧性、叙事语言节奏张弛分明的文体。用它来“写实”,可以吸收传统艺术以动作白描为主的写法,可以吸收西方深入挖掘人性的心理用笔。非左翼的现代派诗人卞之琳就称赞沙汀道:“要说写实,这才当真做到了。”(《读沙汀小说〈淘金记〉》)那意思是一般的“写实”还远远不够格。无独有偶,茅盾说“沙汀的作品在那时才是货真价实的短篇”(《短篇创作三题》),也是说许多人的短篇还不够真正的短篇。够个“货真价实的短篇”的标准是不易的,但沙汀做到了。
我还要添点蛇足。在“独尊现实主义”的日子过去之后,我们不能再用“流行观”来看待历史上走马灯一样晃过去的文学运动。像有些人所持的“过时论”:今天现实主义“过时”了,现代主义便当兴起;明天现代主义“过时”了,后现代主义就成了能打倒一切的法宝了。这是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实际的历史是下一个浪潮汹涌打来的时刻,即之前的一切浪潮纷纷沉潜的时候。沉潜并非消失。更何况“现实主义”是一种富有弹性的能容纳各种其他创作方法的方法,他今日能潜伏,明天必浮出。并且,“模仿——写实”,又是文学的基本手法之一,就像“抒情”、“象征”是基本笔法一样,是会永远存在下去的。所以依我之见,沙汀可读,沙汀永存。
以上,趁着钟庆成编书的机会,我谈点对现代作家当下意义的看法。并不单在沙汀一人,但沙汀确实是我始终喜读的作家。沙汀的时代毕竟是一个至今仍让后人景仰的文学时代呵!而本书与此前的任何一种沙汀选集的编法都不同,它兼选小说和散文,基本是短篇,也有少许的长篇节选。全书选得简要得当。为便于一般读者把握,又分了若干栏目,以使头绪清晰。这是一个好选本,相信它定能促使下一代的青年读者更好地阅读沙汀,走近沙汀。
权且为序。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