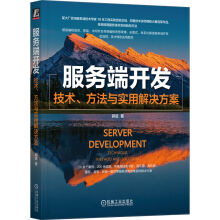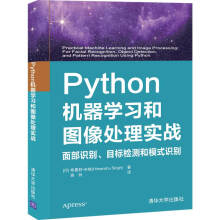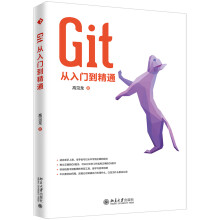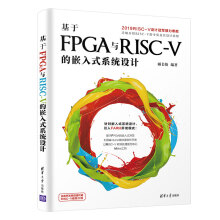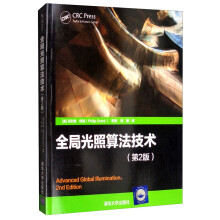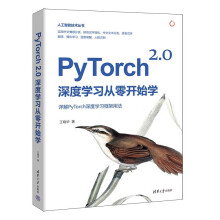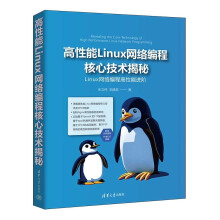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倡导建设性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伴相随,共同建造了一座文学的辉煌殿堂。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在探寻文学批评所起的作用和功能,这种探寻尤其是从初步确立起文学批评的主体意识后,就从来没有间断过。文学批评的作用和功能显然不可能是单一的,但文学批评家会侧重于发挥文学批评的某一方面的作用和功能,这取决于文学批评家的批评姿态。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法官与导师的姿态统领着文学批评的园地,大多数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在解释文学批评时,也都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分析和判断的活动。众多的文学批评家认真履行着法官与导师的职责,但他们的工作不见得会让作家们买账,因为文学创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精神活动,文学作品是一种充满玄机的精神产品,要对其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非易事。并非人们不接受文学批评家以法官与导师的姿态出现,问题在于,在这种姿态下,文学批评家是否站在公正的立场,以什么为评判的标准,却是难以统一的。公正的立场,评判的标准,这就涉及到文学批评家其他方面的素养。当一名文学批评家的思想准备、知识准备以及道德准备难以让人们信服时,其批评就难以被人们接受。托尔斯泰就讥讽批评家是“聪明的傻瓜”。有的作家则声称他们根本不读文学批评。如果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长期处于这种对立的状态,文学批评的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文学批评中的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似乎就注定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只能处于对立的关系。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为了解决创作与批评之间的对立关系,他干脆主张由作家自己来当批评家。他将文学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所谓大师的批评,也就是指那些能够称得上“大师”级的作家所进行的文学批评,也就是作家自己来当批评家,蒂博代最为推崇大师的批评,他认为,大师们既然是作家,就会努力站在作者的立场上进行批评,他看待别人的作品时,就会有一种理解和同情之心。说他们的批评“是一种热情的、甘苦自知的、富于形象的、流露着天性的批评。”按蒂博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职业的批评家都要失业,而作家从此兼上批评家的职责,大概也就无暇顾及创作了。蒂博代的办法并不高明。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批评者是作家的身份还是职业批评家的身份,而在于采取什么样的批评姿态。文学批评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基本上是以法官和导师的姿态出现的,这是与人们的认知思维的历史处境相适应的,在人类文明的创立阶段,人类主要面临的任务是对未知世界进行认知和判断,文学作为一门人类自己创造的精神产品,同样需要进行认知和判断,因此文学批评首先承当起了认知和判断的功能,这就决定了文学批评家最初所采取的姿态是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但是,随着文学观念的成熟,随着现代思想的深化,人们对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有了逐渐深入的把握,意识到不能停留于简单的认知和判断,否则会有损于文学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文学批评家逐渐觉悟到,法官和导师的姿态不仅得不到作家们的广泛认同,而且也无助于文学批评的正常开展。因此许多文学批评家在批评的姿态上做出了调整,采取了一种对话和交流的批评姿态,通过文学文本与作者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达到审美的共振。
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代以后的认知世界的趋势。德国哲学家马丁o布伯在20世纪初就认为,“你-我”、“我-他”是两种基本的人类关系,“你-我”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关系,每个人都需要通过“你”而成为“我”,因此人与人之间通过对话而获得相互性的尊重与追求。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也论证了个体所具有的通过自我、他人进而在更高层次上理解普遍性实体的可能性。巴赫金发现了对话的三个基本特征:开放性、未完成性和语言性。他认为,人类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性的,而生活是无限的,不可能终结的,对话总处在不断运作的过程之中,产生了不同的意义,永远是多种声音的对话。哲学家们意识到,对话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探索的方式,哲学通过对话来打开一个新的视域,新的创造便寓含在这一过程之中。对话和交流吻合了多极化、多样化的文化形态,是哲学发展和创新的有效途径。
这种对话与交流的关系也同样表现在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领域。因此,从法官和导师的姿态到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是文学批评家在姿态上的一种进步的表现。对话与交流的批评姿态改变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关系状态。在法官与导师姿态阶段,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交流,但这是一种单向度的交流,是批评者向批评对象施予式的交流,因为当批评家采取法官与导师的姿态时,就预设了一个真理掌握者的前提。而在一元解读现象破灭以后,那些以真理掌握者自居的批评家反而遭到了人们的抵制。对话并不是自说自话的众声喧哗,而是作者和读者之间以及读者与读者之间面对一个具有客体化内容的文本在一定的语言、文化共同体内进行的协商。因此,对话既包括对多元性与差异性的追求,也表达着对宽容与共通性的渴望,是一种交织着主动与被动、多元与一元、断裂与联系的复合过程。如果说批评的本体价值在于建构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建构又是以作品意义的阐释为基础的,那么,阐释作品意义的途径对于批评价值的实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托多罗夫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当代批评所作出的调整,他说:“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汇合。”
当文学批评家采取对话与交流的姿态时,批评的功能也相应地做出了调整,批评不再侧重于是非判断,而是进行一种建设性的探寻。蒂博代明确地否决了法官的姿态,他之所以对职业的批评颇多贬义,就在于他反对职业批评家以法官自居的传统,但他没有找到克服法官弊端的好办法,只好让作家来接替批评家的工作。德国文学批评家赫尔德的办法就高明些,他的办法就是强调交流和对话,他认为“批评家应当设身处地去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怀着作者写作时的精神去阅读他的作品,这样做有困难,然而却是有道理的。”当他以这样一种交流和对话的姿态去进行文学批评时,自然就会立足于建设性,因此他说:“我喜欢我所读的大多数作品,我总是喜欢找出和注意值得赞扬而非值得指责的东西。”当然,建设性包含着赞美和肯定的意思,对作者所作出的努力和创新给予赞美和肯定,但建设性并不意味着为了赞美而赞美,建设性强调的是对文学作品中积极价值的发现与完善。也就是说,批评家即使需要进行赞美,也是建立在积极价值基础之上的赞美,而绝不是溢美之辞;另一方面,出于对积极价值的完善,批评家也会对批评对象进行批评,指出其不完善之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对话与交流的批评姿态虽然不再侧重于是非判断的批评功能,但并不是彻底放弃判断,而是通过建设性的方式来传达判断。中国现代的文学批评家李健吾就是力倡批评的建设性的,他对建设性的理解是:“同时一个批评家,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犹如我们批评的祖师曹丕,将有良好的收获和永久的纪念。”李健吾将“摧毁”与“建设”对举,更加突显了建设性批评的终极目的,也就是说,批评的目的不是要把批评对象当成敌人将其摧毁,而是要把批评对象当成有价值的东西,同时要与作者一起共同将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建设好。这就决定了批评家的温和善良的批评态度:即不是从恶意出发,而是从善意出发;不是从否定和摧毁对象出发,而是从肯定和扶持对象出发;不仅从自我出发,而且从能够兼顾他我出发。在李健吾看来,以建设为宗旨的批评可能会用上赞美和恭维,但批评不是“一意用在恭维”,“一个批评者应当诚实于自己的恭维”。既“用不着谩骂”,也“用不着誉扬”,而必须做到“言必有物”。鲁迅是一位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家和批评家,即使如此,在鲁迅的批评观中,同样注重建设性。鲁迅说:“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了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鲁迅的比喻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建设性的意义。如果说批评家面对的批评对象只是“满天星”的野菊花,但它毕竟是“佳花的苗”,那么,建设性的批评就是要指出它的潜在的价值,指出它能够培育成“菊花”来的潜在事实。建设性批评的背后透露出文学批评家的善意。尽管不能断然说凡是破坏性的批评都是出于文学批评家的一番恶意,但一个批评家如果怀着恶意的姿态去进行批评的话,他的批评肯定是不具备建设性的。因此鲁迅尽管在批判中毫不留情,但他对恶意的批评家却是非常反感的。他说:“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鲁迅坚定地表示,对于这样的恶意批评家,“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