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登白朗峰之前,我早就看了格林德尔瓦尔德,很容易接触的一处冰川,周边保持原态,不像许多别的冰川那样,修理得面目全非,过分营造了人为的效果。格林德尔瓦尔德冰川,我是猛然间看到的,没有思想准备,突然惊现,未加思索,也没有联想文学的篇章:文学的记忆,在这里不但毫无意义。还会歪曲真实的印象。我的第一反应是:它天真而强烈,既惊异又恐怖。
清晨,我离开了喧闹的因特拉肯镇,以及汇聚在那里的庸人,来到格林德尔瓦尔德村,下榻在一家设备极好的旅馆。一进客房,里面不亮堂,也不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而,当店家打开一扇窗户,我转过身去……这扇窗户,一下子灌进来阳光。在我看来,狭小的窗框漫溢进来的不知何物,庞大、耀眼,还在运动,径直朝我冲来。
的确,从未见过如此奇妙的景象。这是一片光海,似乎就在玻璃窗外,势欲进来。涌进来的强烈效果,不亚于一颗流星突然陨落在地球上,撞击出炫目的强光。
第二眼,我看到这个庞然大物离得并不很近。它那样子似乎在向前进,但是在相当远处及时停下了,还在我步履能及的地点。怪哉!它静止不动,却恍若在运动中!它行进在半路,仿佛被逮住,就地僵硬石化了。
这种景物必须远观,近看没有虚无缥缈的诗意,却会觉得无比粗糙,无比崎岖,无比艰险。试想一下,有一条脏兮兮的白色大路,也许宽达两公里,布满深沟辙道,坑坑洼洼,极为颠簸。从那里驶下来的,是什么样可怖的马车,或者是什么样的魔鬼车呢?在那之间,立着许多水晶体,并不晃眼,倒像一张甜甜的面孔,高约十五尺到二十尺,呈现一种灰白色,有一些则近乎浅蓝色,如同某种酒瓶绿,色调暖昧而凶险。
这面斜坡,显然是很大一片冰海的一次倾泻,而那冰海的边缘,看得见就在山巅,一条生硬的线印在蓝天上。整个景象辉映着阳光,有一种原始的坚硬,是对我们居住在下面的人极大冷漠的结果,我可以这样说吗?是一种有恃无恐的态度。因此,我丝毫也不感到奇怪,就连索绪尔那样平和、那样明智的人,登上这冰川都不禁义愤填膺。——同样,我也深深感受到这些原始巨物的蔑视和挑衅。我相当粗暴地对它们说:“你们不要这样目空一切!你们生存的时间比我们长久一点儿。然而,山啊、冰川啊,在我们的思想高度面前,你们这一万尺高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打算走到近前看看冰川,于是从村子往下走,到达它的边缘,再深入进去。人口有各种各样的。此时,冰川开口狭窄,也不高,外观明亮而光滑。进到里面,处处滑溜,还有危险的斜坡,不知滑向何处。斜坡上方,有两三层淡蓝色的拱顶,开裂的缝隙,看上去很刺眼,那种透明提示人们留神点儿。最意味深长的,莫过于有一簇美丽的花,经过多少岁月,一直镶嵌在那里,透过冰显示它那鲜艳的色彩。在那里禁锢,就肯定能保存下去。这种丧葬的长久展示,比任何死亡的形象都更令人惊心动魄: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永生,可悲地扮演着生命,永远也不可能返回大自然,回到休息的状态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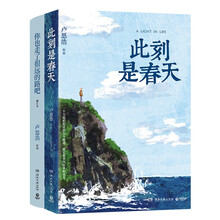








--埃米尔·左拉
米什莱赋予大海一种朦胧的动物性、一种有意识的母性:他讲述这些事物,有他独特的语言,每句话都打开一个深渊。
--皮埃尔·洛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