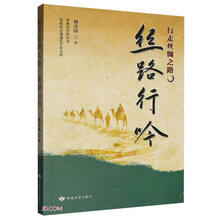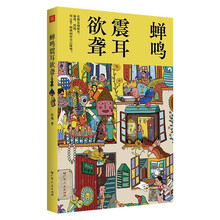跨人校门之前,还得经过一个小的分岔口,这里支着一个简易凉棚。长方形的抽屉上摆满了玻璃瓶,里面盛满各种零食。无论上学,放学,还是课间休息,甚至上体育课,我们都乐意来这里溜一圈,花几分钱,买一杯瓜子,豌豆,或者几颗姜糖,几片生姜,装进荷包,边走边吃。天热时,还可以用自带的盐水瓶在这里灌一瓶粉红色的糖水。凉棚的主人是郭老师的母亲,我们都叫她郭家婆,偶尔,也会亲热地叫一声郭娱驰,那准是我们荷包空了,想找她赊点零食的时候。
不上学的日子,我也会去北街逛一逛,那里有理发店、交易所、缝纫社、茶馆、粮管站,这些建筑和南街的连成一线,依次排开,高低错落。尽管有的建筑只不过用木头搭起来,老旧而简陋,冬季一来,呼呼北风刮得门缝吱呀作响,它们却和洋铁铺的敲打,木业社的锯木,电焊的吱吱声,以及清晨的广播一起,奏成鲇鱼须街上最生动的交响。
还有那些或悠闲或忙碌的男女,嗑着瓜子,有说有笑,或叫卖生意,自得其乐,他们和我们一样,普通,微小,与鲇鱼须浑然一体。一些来自周边的乡里人,将自家的鸡鸭蔬菜挑来镇上,讨个好价钱。也有手艺人在街上租个铺面,对着来往行人高声吆喝。书摊和茶馆,则是两个极好的去处。有人大清早就过来了,花一两分钱,坐在小板凳上,一页页翻阅图书,和摊主聊聊书里的情节;或者花一角钱,端坐茶馆,听《说岳》、《水浒》、《三国演义》,与熟络的老倌子扯谈各路见闻,光阴不知不觉间打发了,直到家里喊吃饭才依依不舍地起身。镇上也有一些不固定的节目,玩猴把戏便是其中的一项。隔三差五,一些河南人或安徽人,牵着几只个头不大有些嫌脏的猴子,在新铺子门口,铜锣一敲,就地开张。过往的闲人纷纷聚过来,自觉围成一个圈。猴子表演完骑单轮车或钻铁环,主人双手抱拳,说些谢谢捧场的行话,猴子也跟着主人抱拳致意,随即,在主人的牵引下,端起盆钵向围观者索要。爽快者早早备好了分币,只待盆钵伸到跟前时,往里一掷,听得“嘣”的一声脆响;面子薄的则不等猴子过来,便悄悄离了场,或退到稍远的地方,等下一场开演时再拢来;也有的既不想出钱也舍不得走开,场面不免有些尴尬,不过也无所谓,笑笑便过去了。
开交易会的日子,街上更是水泄不通。供销社临时搭建的油布棚,从南到北,占据多半个街心,汽车拖拉机板车只能绕道而行,或者干脆歇上一段。久未出门的姑娘婆婆,以及邻近的乡里人陆续结伴赶来,一摊一摊地逛,丝质被芯,绣花枕头,上海毛毯,削价的确良,翻皮鞋,牛轧糖,洋铁桶,锑锅子……无论春夏秋冬季商品,吃的用的,或是平常买不到的,这会儿一应齐全。流连于琳琅的新货旧货,合计着口袋里的银两,权衡着划算不划算,约好的回家时间不得不一推再推。返程路上,满载而归的人们,个个欢声笑语,怪只怪身上的钱不够,遗憾只待来年弥补。
鲇鱼须的这些景致,古朴而趣然,构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清明上河图”。每当想起鲇鱼须,它们便会倏地从我脑海里蹦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