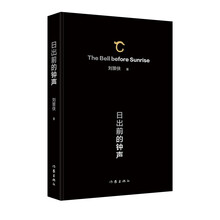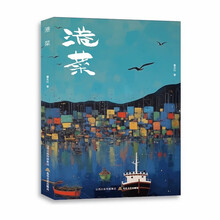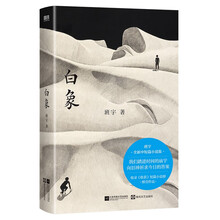秀才陆发家今天迎客。
1905年的绍兴城里,黄包车还刚刚行市,只要有一辆过来,路人就会“喔”、“喔”地惊叫。这不,品芳里旗杆台门里,一清早在家等的秀才娘子李稽听到这惊叫声,说:“陆水来了,陆水来了。”喜滋滋地往台门口走。
黄包车在台门口的石牌坊下嗒地一停,车上跳下一个少妇。秀才娘子迎了上去,说声“小妹来了”,争着给她付了车钱。车夫问:“这样客气,是两姐妹?”李稽说:“我们是姑娘阿嫂。”车夫啧啧称赞道:“你们这对姑娘阿嫂,漂亮得可以入画了。”初夏的品芳里,远山隐隐,近河粼粼,呈水街神韵;茶楼嘈杂,酒肆赌唱,壮堂口声雄。飞檐路亭,日有瞎婆词话,新词与妙曲共远:斗拱台门,夜闻尼姑宣卷,清境同佛理相融,更兼笛韵悠悠赏心,越调娓娓动听,文采风流,时时映衬湖光山色;人烟稠密,处处不愧水街美称。
品芳里正在开市。一边店家一边河的单面街,家家店堂卸了排门,账房毫无必要地擦拭着坐桌,伙计提着东西往店门口摆,掌柜算计的目光乱射着。五更就热闹了的茶楼,生意好得把茶桌摆到了廊沿。穿着褴褛的渔夫,手拎甲鱼、河鳗之类的昨夜收获,穿梭于茶客中间。刚溜到河沿的一只只小划船,载菱藕、蔬菜、螺蛳、鱼虾、酒酱、柴、米和布绢,无船不商;头戴乌毡帽、红着酒糟鼻的船主们,荡船岸下,寻寻觅觅地找着适宜泊船系缆的所在。摊贩们肩挑手提货物,从东双桥奔来,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回头望一下,他们已把货物在品芳里摆得花花绿绿一世界,且相互碰着头,在借火吸烟了。上灶埠船起了锚,船老大用油光丝滑的嗓音吼道:“到越秀桥、上灶埠头的客人上船哕——开船啦!”正在吃喝拉撒的船客,或立即放下碗筷,或赶忙掇起裤腰,喊着“等一等”,慌忙快速地赶来,晨曦中拖着一群群纷乱而老长的身影。姑娘不禁感叹道:“这品芳里越来越拢市了。”“是的是的,”嫂子说,“现在还好嘞,过一息息,要过去,挤得人只好侧转走了。”“做啥要侧转走?”“你不怕人家吃你豆腐?”嫂子说着,手试向了姑娘一动就抖的胸脯。姑娘格格地笑了起来。
笑声引出了隔壁皮记南货店的南山老板。一见陆水,南山惊喜得不知说什么好了,嗫嚅着嘴巴,好久才说:“怎么来的,你?”这对男女小时历过一番青梅竹马,今日一见,陆水也十分高兴,模仿孩提时代两人玩戏的样子,手指作兰花形向对方作揖道:“怎么来的?小女子是被淮洪逼过来的,南山老板布施小女子则个。”南山听后笑道:“还是老样子,旧性不改。”陆水意在言外地说:“旧性不改怎样,难道你改了?”两人眼意心期的目光肆无忌惮起来。嫂子倒替她们红起了脸,一把把姑娘拖进了台门斗,咬了她一会耳朵。陆水道:“你响一些,我听不清。”嫂子头皮往台门外一扭,见南山进店了,就回转头来稍稍放高一点声量道:“碰这种又臭又辣的雄头要闯祸的——告诉你,他一直在惦记你,说你那个东西他生吃都会吃!”姑娘生气地打了嫂子一下,然后扑哧一声,扭转头有恃无恐地笑了起来。
姑娘一进家门,向坐在花梨太师椅上的男子亲热地喊一声:“二哥!”秀才点点头,懒懒地说:“来了,坐。”秀才娘子横了老公一眼,说:“小妹到了,也不起一起身,屁股被钉头钉着?——小妹,你这里说说也不要紧,懒是懒得来——他!”小妹啪地打开了王星记扇厂制的象牙骨绸折扇,扇了起来,说:“真热。”秀才娘子绞了块凉毛巾,递过去,小妹随便地擦了一把,丢给了她。秀才娘子说:“坐、坐。站着干么?腿脚站得膨膨肿的,为省凳钱?”小妹扑哧一笑,说:“二嫂笑话越来越会讲了。”秀才鼻孔里“哼”的一声道:“她除了会讲笑话,还会什么?”小妹心知肚明,二哥在埋怨二嫂不会生产,结婚十三年了,夫妻俩还是上床一对,下床两个,没有什么多出来。她赶忙把话题一转,问:“小哥怎么还不到,杭州夜航船是一早到西郭的。”小哥即陆善。旗杆台门的同福房,上辈有兄弟两人,老小出外在杭州做师爷,老大守祖业,生有三男一女:屹、发、善、水。老小拜堂十几年,没有生育,就将老大满月不久双胞胎中的小儿子陆善抱养了过去。俗言道,儿子过继,断金断谊,老兄弟俩极少来往,陆善只有为生父生母去世奔丧,才来过两次绍兴,平时,兄弟姐妹极少见面。今天来家,因儿子要报考保定军校,家中缺乏川资,以及各种各类不菲的出支,准备把旗杆台门里早分给自己的一间楼房卖掉,以应儿子赶考之用。
“哼,”秀才鼻孔里又是一声,接着小妹的话语道:“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小的脾气:自己戴不上秀才帽,恨不得对儿子饲书,西郭上岸,会一路走一路向儿子讲讲绍兴,走到品芳里,中饭赶得上就要谢谢他了——你们姑娘阿嫂说说话,我到楼上看看书。”秀才说着上楼去了。
秀才娘子把矮桌小凳搬到了弄门口,摆上了茶水果品,招呼道:“小妹,到这里来坐。今年天时热,这里的弄堂风阴稠稠的,有一上午可荫凉。”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