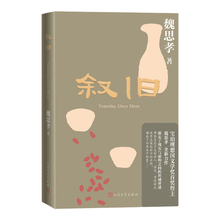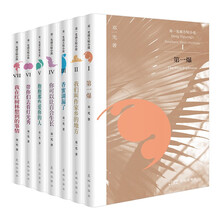本故事结束于异界,却从宇宙开始,“你知道宇宙由什么组成吗?”好多年前,语文老师问,说完伸手示意她坐下,然后转身去砌茶。她注意到掀开杯盖后,他反手将盖里朝天,搁在桌上,“这样便不会沾染尘埃。”老师柔声解释。
这位英俊男子以及他一系列诗情画意的行为举止,令她永生难忘。小心翼翼坐在教员单身宿舍床上的少女,有些痴呆地望着昏幽的阳光从旧式烟筒孔道蜿蜒进屋,形成一个并不规则的圆柱体。
老师也注意到那根奇异的光柱,“是由尘埃组成吗?”若有所思地又问一句。
他走过来,轻轻抓起她的手,把茶杯放在她掌心,“抑或爱情?”她看到他摇了摇头,他继续幽幽道,“无论如何,尘埃和爱情的共同特质是,谁也不挨着谁,但谁又避免不了谁,判断二者的质与量,是毫无意义的。无数的它们,漂泊在跌宕诡谲的空间中,与寂寞之花长期为伍的我,是那亿万分之一的孤独,一次次跟痛苦发生摩擦后,偶然碰撞上了你,便产生了……”睁大眼睛,她聆听他沉醉地吟哦着,“产生了什么呀?”问罢,他微微一笑,把手搭在她肩膀上,白衬衫袖管卷起一半,挽在胳膊中央,参次不齐的褶皱,与细密的汗毛混淆在一起,说,“你看我落在这儿了,对吗?”她不知道该回答什么,感觉他又把那修长优雅的手变换了姿态,那手在她心中如万花筒一般迷离,接着,手又飘向了另一处。终于,落遍她整个身体。“产生了爱……”多年后她偶然发觉忘了这话是他们俩谁说的。
致使少女今生与茶无缘,否则便会回忆起那个杯子,搪瓷上面印着湖蓝色小花,花在何处?在心中否?不清楚,早已凋零残破了。
人亦在偷偷珠黄,他留下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她的儿子,先天性糖尿病让这孩子在学会写字之前,不得不先学会打针。自从懂事以来,每餐后往自己静脉注射胰岛素,是这孩子必修功课。日日如此,小胳膊上针眼密密麻麻,像是生长着一块块藓。
他还留下了什么?是她失意的生活以及情感的落寞吗?没人清楚,也没人关心,但最起码,药首先是儿子必不可缺的,或许是这位母亲长年与众多男人保持某些联系的主要原因。
别忘了还有吃饭,穿衣,取暖,水电,缴纳房租,各种“费”将生活重重包围,无穷无尽,没完没了,让她总算领悟到宇宙到底由什么组成了……总之,什么都有,除了少女时代坚信不移的爱。显然明白得实在晚了,这令她经常感到自己正在迅速衰老,但每天黄昏后,她又拼命设法使自己青春焕发,闪闪发亮。通常下午五点,长发凌乱的她,一觉醒来,宵醉未醒,觉得嘴里又苦又臭。朦胧中爬下床,发现儿子已放学回家了。看到他坐在小凳子上,趴在另一个大一点的凳子上,正写作业。
于是她去给孩子弄饭,把米投入锅中,再用掏米水洗菜。趁着饭还没熟,开始抓紧化妆。已是六点,上班该迟到啦。
岁月流逝与人性消隐,大概物价是最为犀利的见证。那最原始的化妆品,当年的雪花膏,早就买不到了。眼下使用在脸上的消耗品,已经涨到至少几十元。
把几十元钱抹在脸蛋上,去陪男人们坐坐,嘻嘻哈哈喝些酒,换来另外几十元。算算帐,有时比买化妆品的钱多一点,有时少一点,那就“赔”啦。趸来原材料,花心思加工一下,出售,赢利,或者亏损,她确认这行当跟小商小贩毫无区别。
小商小贩的日子,用她的原话说是,“过得够够的了”,但又无力挣脱。当然,客人中间自然也有不少家伙对她许愿能够给她什么什么生活,承诺这生活如何如何幸福,结果无一例外,都是逢场作戏。
她的工作原本就是表演,到头来却成了欣赏他们表演,到底谁演谁看?渐渐地也就不甚了然。
有理由相信她其实也在等待某一男子出现,而男人无处不在,可惜差不多所有男人都一样,全身上下金光闪闪,同时杀气腾腾,仿佛能像超人似的拯救地球,然而她的一位“同仁”说的话把她逗笑了:“他们连生物进化都没完成。”不过是些扑火之蛾,新婚夜被吞噬的公螳螂,拍着胸脯的银背猩猩,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究竟向往什么样的异性?她说不清,若说得清,也便不至落到今日这般境地。几年前曾经出现过一个彻底打动了她的男子,那人的脸完全符合她对一个男人的全部要求,即英俊,可是他的整体看上去渺茫而又卑微,说穿了就是贫穷。
偏巧她一向对落魄潦倒的男人持有独特好感,顽固地相信不饱经沧桑,就没法懂得理解感情。于是暗中观察他,但始终猜不透他属于何人。因为喝醉之前,他沉默不语,那咬着嘴唇的腼腆气质,令她丧失力量再去留意其他事物。但几口酒一下肚,那男人就原形毕露了,他开始狂妄地自我膨胀:“我叫米,你们听说过米吗?迟早有一天,米名满天下。”毫无来由的宣言逗得全体男士哄堂大笑,将《何日君再来》的曲声压了下去,姑娘们也跟着随声附和,但神情十分古怪。男人讽刺男人,目的是清澈的,女人的动机就浑浊得多。
她确定,或者说,她愿意相信米不是自己来这种地方的人。事实也是如此,那段日子,常常是一个戴眼镜的歇顶引米一同步向吧台,然后把他忘记,自己找乐子去了。米独自缩在角落,骆驼一样耷拉着头,颓废的头发乱糟糟地随着打嗝的脊背一起一伏。
这时候她的生意开始呈现走下坡路的态势,对她许愿发誓的男人逐渐少了,搭理米的女人则是一个没有,倒给了这两个人亲近的机会。
但每一次攀谈都使她对这个男人的印象转坏,首先她无法确定他是否清楚自己的职业?画家?作家?拍电影的?还是搞音乐的?反正,“是一个必须出名才能成功的职业,”米晃晃悠悠地说,“今天我又被毙了,该死。编辑,和……”他抬起胳膊把手摆成一把枪的样子同时闭上右眼,砰,搂火,显然他又醉了,他似乎无时无刻不在醉,“刽子手,是同义词,对吧?你为什么不点头呢?嘿,美人,你叫什么?请我喝一杯怎么样?我有的是钱……”酩酊后的口头禅“有的是钱”将他弱点暴露无遗,“你想喝什么?”她苦笑了笑,但诚挚的问。
“随便,只要能让我踢开烦恼。你叫什么?没名字吗?”“我是17号,你就叫这个吧。”她谨慎地回答。
“17号?哈,令我想起了那囹圄岁月……”“囹圄”立刻使这句话含糊而浪漫了起来,她不是特别明白,而他没给她提问的机会,只是一个劲儿地唠叨牢骚着:“进去了,人成了号码。出来了,还是个号码。号码,号码,到处都是号码,男人是个号码,女人还是号码,这是为什么呢?号码,号码,号码,他娘的我的酒呢?”酒来了,米毫不客气,一饮而尽,嘟哝着还没把烦恼消灭干净。一只手示意再来再来,另一只擦拭嘴巴的手中指上的老茧格外粗犷,似乎由于长年握笔。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