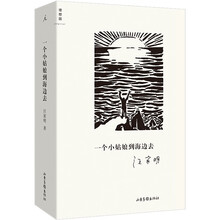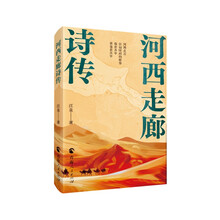(二)明清安徽小说
1.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安徽全椒人。出身于世代科甲的家族中,自幼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生平却最恶举业。他亲身经历了封建大家族争夺遗产的纠纷,看清了封建家族伦理道德的丑恶本质和缙绅人物的虚伪面目,于是与那些倚仗祖业和门第为生的纨绔子弟分道扬镳,成了一个缙绅阶层的叛逆。他在30岁前就将祖传田地房产消耗光了,堕落为“乡里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吴敬梓《减字木兰花》)。在家乡舆论的压力下,他33岁时移家南京,开始了卖文生涯。36岁那年,他托病推辞举荐出仕,甘愿过着清贫的生活,直到客死扬州。
吴敬梓开始创作《儒林外史》是在清朝大兴文字狱的乾隆初年(1736),大约成书于19世纪初。为了便于暴露现实社会问题,他巧妙地选择了明代的某些历史事件作为小说的背景,但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清代基本一致。《儒林外史》描写了整整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命运,对传统文化的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封建社会的颓败也有着鞭辟入里的解析。同时,它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均不同于既往的小说,有很多艺术创新,在中国讽刺小说史上有着“空前绝后”的地位。鲁迅评价:“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中国小说史略》)。
《儒林外史》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科举制度的罪恶。揭露八股科举的弊端,批判功名利禄观念,是《儒林外史》的中心内容。隋唐以后定型的科举制度,使科举成为读书人猎取功名的唯一手段。这种制度到了明清又添加了八股制艺的枷锁,立论依《四书集注》,行文按八股固定格式。八股文形式僵化,一方面适应了统治阶级对士人思想的控制,另一方面也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种文化导向和用人制度不仅造就了一批批飞黄腾达的官僚,而且腐蚀和摧残了一代又一代士人的人性,扭曲了他们的人格。
《儒林外史》对这种八股取士制度中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精神面貌作了细致的刻画和全面的扫描。在明清时代,知识分子做官主要靠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条是科举正途,另条是因博学多才或操行卓越而做名士。由于科举的名额有限,或由于科场的不如意,有一些人放弃科举后,仍不愿放弃知识分子的架子,自命清高,冒充风雅,自命为“名士”。这种封建文人的典型特征在《儒林外史》中得到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批判。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中曾经指出:“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在小说中,与功名富贵观念相对立的,是作者所标举的“文行出处”(指文人的学问、品行和对待出仕、隐退的态度)。在小说的开篇,作者曾借书中人物王冕之口,说出了自己的观点。王冕看了秦老带来的“一本邸抄”中有一条“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不以为然地说:“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热衷功名富贵还是推崇文行出处,是小说作者臧否人物的主要标准。正是按照这个标准,作者是把书中人物分为真儒、假儒,真名士、假名士几大类型。无论是热衷科举功名的范进、周进,还是科举出身的贪官污吏王惠之流,虽然并非没有读过“圣贤之书”,也不是没有听说过“先王之道”,然而,其所作所为则是对儒家传统文化的最大嘲讽和背弃。如果说范进、周进等科举迷们既没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又没有承担提倡礼乐仁义的责任意识,变成唯八股是窥,唯功名是求的委琐、麻木、病态的陋儒的话,那么,王惠、严监生和严贡生等人,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更是一批鲜廉寡耻、贪得无厌之徒,是彻头彻尾的假儒。至于那些科场败北、功名失意,却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的假名士,则更是一些社会的废物,他们不学无术,而以风流名士自居,靠胡诌几句歪诗沽名钓誉。
知识分子这种存在状态的罪恶之源当然就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用八股文取士,就是让读书人死抱住“四书”、“五经”不放,终日揣摩那陈腐的八股文作法,一切经史上的大学问和人情世故全然不管。于是,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就是一大堆浅薄无知、头脑迂腐的书呆子、废物。周进曾经赞美范进的文章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是这位范进,却连苏轼是何人都不知道。那位当过知县的举人张静斋和现任知县汤奏,连本朝初年的刘基都不知道,还在那里高谈阔论,冒充渊博。马二先生是小说中一个比较正直的读书人,只因中了科举的毒,成了科举至上主义者,竭力劝勉别人致力于科举,自己则变成了一个迂腐不堪的人物。可见封建纲常观念已经深入天下读书人的骨髓,使他们成了封建礼教毒害下的行尸走肉。
封建科举制度最深层的毒害恐怕还是对士人人性的异化与扭曲。小说用了较多的篇幅描写了这种情况。最著名的例子是匡超人。匡超人本是乐清县一个小户人家淳朴善良的孩子,靠劳动维持生活,极孝顺父母,敬重长辈,和哥嫂邻里相处得也很好。可是一读了点书,有了点际遇,便得意忘形起来。他先是受马二先生“举业至上主义”的毒害,又学会了景兰江等假名士的一套吹牛拍马的本领,后又跟随狱吏潘三等市井恶棍学到坑蒙拐骗的手段,中了举后,竟坐地分赃,迎新弃旧,忘恩负义,完全变成了一个势利小人。刘浦也是这样一个货色,才读了点书,便冒牛布衣之名,自称文坛名士,与官府交结,要他的舅舅来给他当仆人,侍候董知县。范进也是这样,中举后不久,伪君子的面貌便显露出来了。那些读书人闲居乡里,便是土豪劣绅,做的都是害人掠货的勾当,如严贡生那样的恶棍,阳奉阴违,巧取豪夺,招摇撞骗,唯利是图。
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还体现在知识分子人格的虚伪上。《儒林外史》第十回写生员景兰江对与他初次见面的秀才匡超人夸耀自己的学问:“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讲八股的。各处诗选上都刻过我的诗,今已二十余年。这些发过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们唱和。”景兰江以名士自居,实则胸无寸墨。这些人聚在一起吟风弄月,自我吹嘘,互相奉承,与其实际诗才,毫不足称。第十八回中被称为“江南王谢风流,天下第一个才子”的雅士杜慎卿在人前,抱怨:“妇人哪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臭气!”(第三十回)然在背后却叫媒婆跑遍全城,替他寻找标致的姑娘做妾;他一面说最厌人们张口就是纱帽,一面却又准备下几千两现银以备科举考试使用。这是一个“雅”得矫揉造作而终不能免“俗”的纨绔公子,簇拥在他周围的那群所谓名士是什么货色就不言而喻了。
人性的丧失是封建科举带来的最大罪恶。王玉辉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而几乎丧失了人性的迂拙夫子,他的女儿死了丈夫,她表示要绝食殉夫,她的公婆劝她“快不要如此”,可王玉辉不但没有劝阻,反而大加鼓励,说“这是青史留名的事”!女儿饿死后,她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王玉辉竟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只怕将来我不能有这一个好题目哩!”这里没有坏人的引诱,也没有环境的逼迫,却是一种隐藏得很深的、顽固的封建道德力量在起作用,它使王玉辉的女儿自觉从容殉夫,使王玉辉丧失了正常人的人性与人情,以一种变态的心理、麻木的精神做了杀人礼教的帮凶。在礼教的桎梏里,正常的人性人情都被完全窒息了,这就充分暴露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和虚伪性。
《儒林外史》的艺术魅力还体现在它深深的悲悯情怀。致力于科举,为的是猎取功名富贵,跻身上层社会的行列,而那些考不上的穷书生,境况却是非常凄凉。小说写了几个这样的人物。一个是倪霜峰,二十岁上进学,做了三十七年秀才没有考上举人,“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一日穷似一日”,只得靠修补乐器过活,养了五个儿子,有四个都卖到他州外府去了。周进读了一辈子书,六十多岁不曾进学,教乡村私塾过活,每日只得二分银子吃饭,被入过学的梅三相公和王举人奚落过。王举人到他私塾里歇宿避雨,撒下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后来人家嫌他迂腐,书也教不成了,“在家日食艰难”,他姐夫也奚落他说:“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到几时。”后来是帮人家记账。读书人潦倒至此,怪不得到了贡院里,触发起一生的苦楚,便哭得死去活来。而当几个商人愿拿出银子给他捐个监生去应考时,他竟说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接着,趴在地下,磕了几个头。范进比周进更可怜,五十四岁了,冬天去考试,穿的还是破麻布,被他岳父胡屠户骂为“现世宝”、“穷鬼”。他到省里去考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还等着他回来卖老母鸡买米煮粥吃。这些人中举后就不同了,周进做了考官,“绊袍锦带,何等辉煌”;范进则是“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在这样的社会里,读书人的命运,取决于几篇能否被考官看得中的文章,一举成名后的鸡犬升天固然值得批判,但作家对十年寒窗艰难和屈辱的展示仍然充满悲悯的情怀。
尤为可贵的是,批判与揭露并不是《儒林外史》的单一主题,它也在反向探索着知识分子精神重建的维度。它在充分揭示封建科举这个人性桎梏的同时,也表现出呼唤真实自然完美人性的回归、维护心灵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深刻主题。小说首先通过塑造王冕这个正面形象来“敷陈大意”,“隐括全文”:他是一个“真儒”,天文、地理、史经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主张仁政,要求王者以德服人;他出身田家,鄙视功名富贵,不求官爵,不慕名利,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过着自食其力的清贫生活。杜少卿也是一个闪耀着时代光辉的形象:他不守家业名声,拒绝应征出仕,背离了科举世家和特权阶层为他设定的人生道路;他在治学和日常生活中,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追求恣情任性、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显然,作者是将王冕、杜少卿作为自然完美人性的理想化身来刻画的,并且借这些人物形象来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爱憎感情,呼唤人格的独立尊严和人性的自然完美。
《儒林外史》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段等方面均不同于既往的小说,表现了鲜明的艺术创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