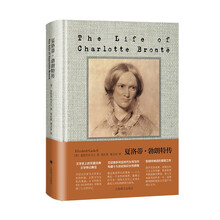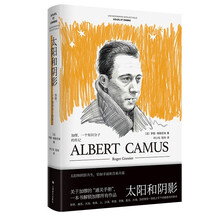对闻一多的变化,罗隆基、朱自清、吴轮晗等友人都曾不约而同地做过类似的分析。罗隆基当年说过闻一多有三变:从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变为30年代的书斋隐士,再变为40年代的革命斗士。
朱自清也谈到闻一多的三变:“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八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1948年开明书店初版)
吴晗说:“闻一多有三变,但他永远在进步,永远在追求真理,到美国求学时代,他学画、学文学,回国后他又以新诗人出现于文坛。中年转变方向,研究诗经楚辞,搞甲骨文,金石文,成为古典文学研究的权威。再一变他不写诗了,也不许可他再做研究工作了,全部时间和精力贡献给民主运动。有人问他是否有第四变,他回答是不会变了,因为已经走上追求真理的路了。”“这个诗人、学者、教授被赶出象牙之塔,被赶到十字街头,到了十字街头以后,他走上为人民服务,领导人民斗争,争取和平民主的大路。”(吴晗:《哭亡友·闻一多先生》,1946年7月28日昆明《学生报》)
这些分析在时间的划分上,虽略有差异,但由诗人到学者到斗士的结论是一致的。在闻一多变化的每一个阶段,他与郭沫若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诗人时期,郭沫若几乎成了闻一多的“偶像”,无论是交友、写诗、出书、办刊,都与郭沫若比照:交友上,他要以“令人景仰”的郭沫若与田汉“缔交的一段故事”为榜样,“勇气”十足地和顾一樵等人订交;在写诗上,要“像沫若”一样,“雄浑、沉劲”;出书上,他的《红烛》“纸张字体”都要“照《女神》的样子”,尽快“送出去”,以便“叫响”自己的著作,“领袖一种文学潮流或派别”;在办刊上,要避免“寄上篱下,朝秦暮楚”,“湮没”个性,“急欲借杂志以实行”文学的“使命”,“以与《创造》并峙称雄”。学者、斗士期间,两人虽远隔千山万水,但精神始终联在一起,旗帜鲜明地相互学习、支持,共同创造。难怪郭沫若要说: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