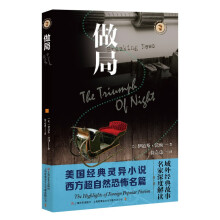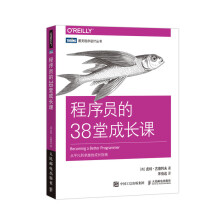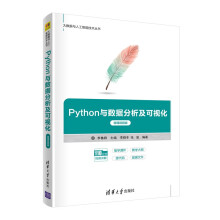在我最初制作高端人物访谈节目的时候,曾深受香港电台的《杰出华人》系列的影响。最富成就的人物,扎实生动的内容,有一定深度的对话就是我对节目的要求。头两年节目以“成功故事”为主,谁有名就采访谁,什么传奇就谈什么。慢慢地,开始不满足了。无论怎样传奇,无论多么重要,都不一定与你我相干。再说,新闻已经报道过,历史已经评价过,还要你再说一遍?面面俱到地报年谱,又能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呢?我苦恼着,一遍遍回放采访的录像,结果发现,那些经得起反复回味的片段往往与所谓的成功结果无关。它们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激动瞬间,不是艺术杰作被天价拍卖的屏息时刻,而是与过程相关的一个个困境,是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当事人的彷徨无助,以及在苦难中体味的细微温情,这些才是人性的相通之处,是大浪淘沙后留下的烁烁真金。
于是这以后的采访,我有意识地多谈“人”,少谈“事”,多谈“困境”,少谈“成功”,以期找到被采访人与观众的共鸣。当我问何时找回心灵的安宁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告诉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决定告诉妻子真相。真相给人自由……我从我的母亲那里学到了在逆境中生存的勇气。她常说,人生中不顺利是常态,顺利才是暂时的。”这世界上口才比克林顿好的实在不多,但我相信他的话语是真诚的。同样地,我能够体会成龙的真诚。他在我就“小龙女”事件旧事重提的时候说:“我真的一直防着我太太,因为我怕她把我的财产卷走,我一直只给她够用的零花钱而已……那一天,我给她打电话,没好气地告诉她我发生的事情,我希望她生气,希望她骂我,然后我就可以说,算了,离婚吧。但她没有,反而让我别管她,先去把别人照顾好。我傻了,真的傻了!后来,我就改了遗嘱,把财产的一半交给她,另一半捐给基金会。”我一边采访一边想:“可怜的女人,她本来就应该得到你的财产的那一半。”但我没忍心打断成龙的叙述,他的感动和他自我感觉的“慷慨”都是真实的。
有时,成功本身就是一种困境。近几年我采访的人士中有不少是我认识多年或曾经采访过的,如陈天桥、江南春。他们走过创业初期的艰辛与惊险,一步跨上纳斯达克的这匹快马,飞扬的股价、高涨的业绩使他们成为资本的宠儿。不过,还来不及高兴太久,这匹烈马就使出了顽劣的性子,它的贪婪、喜新厌旧和冷酷无情让人不寒而栗。
还有一种困境,叫万众瞩目。如陈凯歌、冯小刚,如妮可·基德曼、休·杰克曼。当初人们那个捧啊,曾经人们那个损啊,哪里有你辩白的余地?妮可刚踏人好莱坞,采访期间相传她不过是傍上了汤姆·克鲁斯,试图走捷径的美妞而已;陈凯歌拍了《无极》,故事的确牵强了些,受到揶揄后,用词也意气了些,谁料得到这引来山摇地动的“馒头”风暴,真能将人活吞了似的。人一旦受到过度的关注,就成了某种象征,周围人对他(她)的评价往往就夹杂了许多其他内容,当事人大概只有一边挨着,一边向上苍祷告。
比外界压力更难受的一种困境叫自我怀疑。哲学家周国平是位智者,就连他也逃不脱这种困境,甚至因为敏锐善感,他的痛苦比旁人还要来得更深切些。当他一个人被下放到偏远的小城,寂寞难当,他有理由怀疑自己是否会终老于此;当他高考返城,在婚姻之外邂逅爱情,他长期在责任和情感的选择中辗转难眠;当他心爱的女儿妞妞在婴儿期就被诊断得了绝症,他和妻子就不得不为保全女儿的眼睛还是生命而痛苦选择。这生命的难以承受之重,旁人又怎么体会?哲学,又如何能帮得上忙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