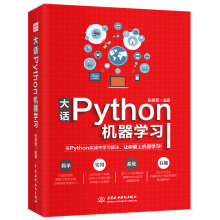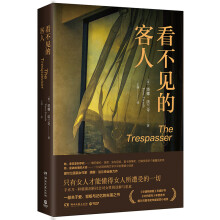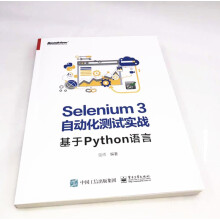在暑天的午后走过禁城脚,仿佛是一步涉进绿色的泉。抬头寻望,那一直如毒蜂紧盯额角的酷热,早在一团团繁密的榕叶掸击下,散成了千万点轻灵的萤火。阴阴的青苔沿着石条的接缝勾勒出长方形的网格,欣然滋生着大墙的古老与雍容。榕树的气根垂挂下来,也如耆宿们捋尽沧桑的胡子,在风中沉着轻摇,而衣上的树影便宛然祖荫的宜人了。<br> 这样的感觉简直就是错觉。铺天盖地的热浪就在身后那三块石碑上飞翻涌撞着。但我还是乐意滞留一步,深深地看,泛泛地想,甚至于向古老的条石伸出灼热的手去,企望这一贪念或许会接通那千年的冰凉。<br> 禁城不是地名,至少在在榕城人话语中还不是。口语说“禁城脚”,而上了这“脚”,已是“府衙内”之意,似乎禁城便是外于“府衙”而立于“脚”之上那道“(城)墙”。听说学者之间就连“禁城”,还是“金城”,犹有争论,所以这“名”的问题我们不妨暂放在一边——现实的存在就是那样子,来来往往的人们总会有这么一弯可以沿而行之的高墙。<br> 我不知道禁城高低长短的数字,只知道它在天地之间肯定很微屑。但我们若试着把揭阳的地面放大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那么这禁城按比例大起来,恐怕不亚于万里长城。而按着沉重冰凉的条石,我知道这墙中也垒砌着同样的鞭影、哭声与智慧。这就是历史么?或许还不尽是。仰望墙头那一排势欲撑天的榕树,我却记起一个关于榕树繁衍的说法。<br> 据说榕树那粉红色榴籽大小的果实是鸟类最喜欢啄食的。榕籽被鸟们消化掉肉质,坚硬的种子裹在鸟粪中被排泄在墙头,一旦得雨露沾润而生根发芽,一株墙头榕就诞生了——虽然禁城上的榕树不一定如此出身,但我总以为墙头榕最能象征历史——在现实与未来的移步换形中,一长溜过去的故事结成滋味各异的果实,浓缩着人世种种的苦难与勋业。若不是经过了时间之鸟的啄食消化,依靠了一代代人生命的撑擎,在腐朽与神奇互化间不断发出蓬勃的生机来,那么历史于我们还有什么意义?禁城和禁城上的榕树,匆匆往来想或不想的行人,身后的碑记和前面的阳光,仿佛便影缩了两千年古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身披榕影的人们,脚下这一步举起,却同时完成着直线的位移与时空的寰转,循环的焊点能否积叠起更高的层数?民族、社会、文化、文明,人类历史的所有进程其实都是如此,只是那规模要成千倍万倍地扩大了……<br> “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已经是一句老牌的名言。但我们的理解是否匆忙了一点?至少在念这句话时,语气的褒贬是否经过了推敲?辩证法的剖析应该也适用于名言的,关键就是在主、谓、宾之外你怎样给出个定、状、补来。长城的意义很多国人在思索,禁城的重量却只有靠揭阳人自己来掂。机械的记忆和浅薄的背叛,其结果如何我不敢设想,但捧一颗榕籽毅然举步的乡彦,无疑正走向前方那火辣辣的太阳。<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