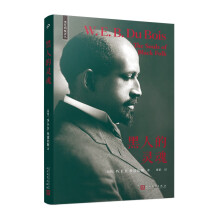诗人们或忧国忧民,或风流倜傥,煌煌千年的中国文学史,何曾有过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又何曾有过一部惠特曼式的自己之歌?中国传统文化对个人生命的压抑、束缚,使中国人的生命变得如此虚伪,如此之丑,以至当诗人们终于敢于正视自己内心真相时,他不得不写着“丑的”、“非诗”的诗。当代诗人这样拒绝再与那些少得可怜的所谓高尚的人格面具认同,拒绝凭借那些在传统观念上所谓“美好的东西”来掩饰个人生存状态的真相的自觉,使他们在新诗兴起七十年后,终于开始从本质上与传统决裂。如果中国已持续十年的改革,最初几年还只是在政治、经济方面显示巨大影响的话,那么诗歌中这种个人内心生活向世界的开放,恰恰预示出我们时代开放求实的伟大改革,已经进入到更深的层次。个人生命的自觉,是西方文学早已丧失的大陆,而中国,千年来这块大陆是封闭的。而今天,中国诗歌对这片大陆的探险已经开始。
这些诗歌看起来似乎是:自虐的、反讽的、黑色幽默式的、陌生化的。这种结果与其说是诗人们故意为之,是一种写诗原则,不如说它是个人生命的自觉和传统人格面具、审美习性相冲突的结果。中国传统诗歌的审美风尚强大到这种强度,以至只要诗人照相式地描述一下内心生活的真相,就使诗人被人们视为最具有先锋意识的现代派。
在这些诗歌中,我看到一种冷静、客观、心平气和、局外人式的创作态度。诗人不再是上帝、牧师、人格典范一类的角色,他是读者的朋友,他充分信任读者的人生经验、判断力、审美力。他不指令,他只是表现自己生命最真实的体验。这些诗歌表面上看来是冷漠的、非抒情的、毫无意义的,然而它在那些好的读者看来,却是有生命的、有意味的,它的客观性使读者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呈现一种多义的审美效果。
这些诗使诗再次回到语言本身。它不是某种意义的载体。它是一种流动的语感,使读者可以像体验生命一样体验它的存在。这些诗歌是整体的、组合的、生命式的、一直流动的语感。它不可分割,也无法破译,如果你在它本身之外,仍然感受不到什么的话。在传统诗歌中,一些句子是另一些句子的仆役,人们因而得以编《名句选》一类的东西。这些诗以一种同时代人最熟悉、最亲切的语言和读者交谈,大巧若拙,平淡无奇而韵味深远。它的韵律是自由平实的、交心似的,它和诗人内心的节奏息息相通。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