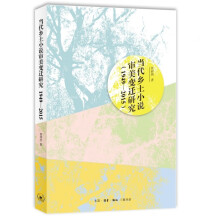德里达等人的理论被我国某些“文化批评”的倡导者概括为“反本质主义”用来作为颠覆文学理论、宣扬“文学终结论”的武器:说什么凡是对于本质的探讨都必然导致“在本体上,它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可以变化的‘本质’,而是假定事物具有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普遍性/绝对本质。表现在文艺学上,就是认为中外古今的文学都具有万古不变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以前已经先验设定,否定文艺活动的特点与本质是历史的变化、因地方的不同而不同。在认识论上,本质主义坚信人只要掌握了科学、理性的分析方法,就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对于本质的认识,否定知识(包括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从而把“五四”以来我们参照和吸取了西方科学思维方式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关注文艺本质探讨和研究的文学理论都与“本质主义”捆绑在一起来加以批判,而导致出现了在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较为普遍存在的排斥理论的倾向。如果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当刘再复以“希腊神话中的床”(按:即指“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来比喻文艺理论时,所指的还只是以“政治裁判官形式”出现的那种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理论;那么,在今天,则被有些学者不加区别地几乎一概予以否定。以下的一些言论我觉得是较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如有的学者认为,文艺理论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文学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本质,如同千变万化的水都是HO一样,……只要理论家提炼出这种本质,文学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所以他把“理论家的工作程序”看作是“先给某些概念规定种种定义”,然后“再用这些概念来衡量具体文学现象”,就像“先掘了一个坑等待一棵合适的树”那样,其结果也就必然会“滤掉那些没有本质意义的外围现象”,去寻找“一种独立的、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文学语言结构”。但由于事实上“文学不是按照本质设定的理念范式发展为实现理想的本质的”,因而他们因此认为文艺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人们“幻觉的蛊惑”,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