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萌(1949—2006),湖北省武汉市人。五十年代中,父亲曾卓被最高当局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家庭生活发生剧变。文革中,她和同伴以大字报的形式对当时的政权和时局发表了为主流意识断不能容的文章,遭到抓捕、审讯和监禁,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押送鄂西北的大山沟监督劳改。六年后终获平反。1979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欧洲文学史专业硕士学位,从事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研究。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94年,调入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历任副研究员、研究员、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所长、外国哲学重点学科带头人、研究生导师等。
著作有:《升腾与坠落》《人与命运》《临界的倾听》《断裂的声音》《情绪与语式》等。主编《启示与理性》(三卷)和《独自》(二卷)。另有诗作若干篇。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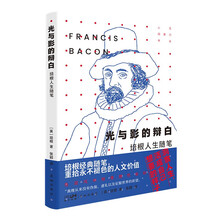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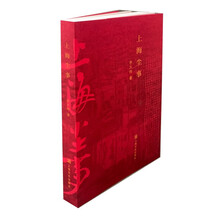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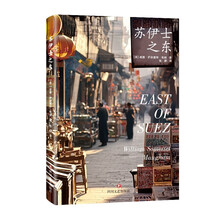
——陈家琪
萌萌想象的那个天堂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但别说想象和记忆是无力的,当它们变成文字,一种不是永恒的永恒就存在了。
——王鸿生
萌萌是一个普通的思想者,但她的逝去会让你产生一个时代已随她而去的感受。力图抓住那个在身边却又已远离的世界,将使一种写作成为悼念。
——耿占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