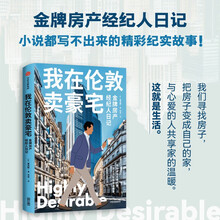一九二七年五月,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长沙又发生马日事变。不久,武汉国民党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记得在军队方面的有“共产党退出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人员不准召开会议和必须受军事指挥人员的指挥”等,这样,共产党员被逼迫退出军队,各处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逮捕、屠杀。
当时我在唐生智部三十六军任营党代表。部队正沿京汉路由河南撤回汉口。我得到消息看情况不好,就连夜趁机逃走。这时,沿线已被反动军队控制,各站都在盘查。
到了广水,天墨黑,盘查的士兵没有发觉我。
我曾在广水铁路工会做过群众工作,认识不少工人。我便打算去工会。路上远远地看见几个工人提着马灯朝车站这边走来。走近时,一位认识我的司机立即招呼我,惊讶地问道:“你还没有走吗?”
“刚从柳林逃到这里,想回汉口,特意来找你们。”
“往南开的都是军用车,恐怕坐不上。”他有些为难地说,其他几个人也都锁紧眉头,面面相觑。我看他们有难色,就说:“那我就走小路吧。”
“那还行?沿路都在查,步行很靠不住,再说,那要走多久呀!”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他忽然大悟似的说:“单开车头出去!”
这话顿时提醒其他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对,就这样干!既秘密,又快。”
我激动地说:“太谢谢你们了!”
时间已经是午夜,初夏的夜风还是透凉的。几个人急急地向车站走,都觉得有种神秘的紧张的感觉。“呜——”的一声,车头飞也似的开出了广水。
车头在黑夜的平野上疾驰。我想到,做政治工作的不让带兵,现在被人撵走、受迫害,连性命都难保,心里非常气愤,如果我们掌有兵权,哪有这样容易离开部队的?
快到花园时,车停住了。那位工人同志好像很抱歉似的对我说:“再不能往前开了,午前我们要赶回去。你一路小心吧!”我点点头,跳下车,说了声“谢谢”,就和他们分手了。
我回到汉口,找到组织,诉说逃回的情景。我对陈独秀政治右倾的做法非常不满。真担心国民党右派一旦叛变,我们将处于无力抵抗的危险境地。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对武汉实行封锁。广东军阀封锁了粤汉路。长江航运被四川军阀杨森封锁。市面上一些资本家及奸商故意罢业,停止贸易。七月十五日,武汉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大规模的屠杀。面对着这种局势,我既焦急又气愤,心想,革命非要有武装不可,我一定要拿起枪来战斗。
经刘力劳同志的介绍,我在贺龙部的特务营当副连长。这个连有一百多条驳壳枪。抓住了枪杆子,我心里着实高兴。以后,我怀着极大的热情随部队到南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
起义后,部队南下向广东进发。八月六日,最后一批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要我留下,了解一下敌人的情况,并设法与袁州(现为宜春)毛泽东同志带领来参加起义的一千多人取得联系,同时,交给我一封给省委的信件,他们就走了。
送走他们回来时,已经是深夜一点多,我将亟待处理的事情办完,东方已渐薄白,鸡啼四遍。我卸去武装带,想眯一会儿,外面就跑进人来,气喘吁吁地说道:“副官长,敌人出来了,省政府被包围了,赶快走吧……”话还没说完,就听见外面“叭——砰”的枪声。我没有料到潜伏的敌人会出来得这样快,就急忙穿上便衣,往大门口走,迎面就碰上敌人持着枪从街上跑来,冲着我问:“喂!里面有人吗?”
“有!”说完我就往街里走,其实里面早就没有自己的人了。
一口气我就跑到西大街光亚瓷器铺。那是一座小店房,我认识店里两个店员。他们是同情共产党的,店里刘老板也见过几面,是个心地善良的中年人。
大家都生怕敌人发觉我。上午,几个人分头出去打听消息,一会儿回来说:“街上已经戒严,在挨户搜查!”我正在思量,老板娘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搜到隔壁来了,唐先生,怎么办呢?”这爿小店只有一楼一底,要藏是藏不住的。我便往楼上去看看,见一个大座瓶,足有四尺来高。真是急中生智,我把这大座瓶放倒,先将脚伸进去,然后缩进身子,满满地装了一瓶。刘老板急忙把瓶扶起,顺手往瓶口上盖了一顶破草帽。
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来,接着就听见刘老板赔着笑招呼:“老总,请检查,我们这里没有别人。”
“没有共产党吗?”
“没有,唔,老总!”
敌人的脚步声听得很清楚。忽然,“咯噔咯噔”的皮靴声踱到瓶边来,我顿时全身一阵滚热。谁知,“咯噔咯噔”地又走远了。他们来回地踱着。我心里又紧张,又愤恨。直到听见下楼的声音,我才松了一口气。敌人最后警告了一番才扬长而去。
一连三天紧闭城门,戒严搜查。城内的情况我了解了,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不能久留,便打算出城赶部队,我跟他们商量。店员路不熟,搔着头在想办法。半天,刘老板皱着眉头说:“路是有一条,恐怕你不能走。”我坚决地说:“只要能出城,什么路不能走呢?!”
“从阴沟里爬出去。”
“行!”我就决定这样走。
店员们凑了几块钱给我,又送了我一套衣服。半夜,刘老板便领着我钻进阴沟。
夜黑黝黝的。沟里的污水半尺来深,臭得人恶心。刘老板打着手电,忽明忽灭。两个人都憋着气,半句话也不说,躬着腰一步一步地走着。走了约莫半小时,走到了城墙外了,趁天亮前的一阵昏黑,我们安然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在离城三十里刘老板的老家吃完饭,我换去一身脏衣服,说了些感激他们帮助的话,就和他告别,向抚州走去。
只我一个人了,去哪里呢?路既不熟,土匪又多,而且周围都是敌人,封锁得很紧。难道革命就失败了吗?不,不可能!海陆丰有我们的队伍,湖南有我们的武装……还有我们的党、我们的同志们!在未死以前,我还是应该想办法找党,找队伍。
空着双手,赤着脚,我不敢走大路,只沿着路旁的田埂走,身上分文没有,饿了就向小摊上要点残食充饥;晚上就露宿在甘蔗地里。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浑身都是一股热酸气。这样走了三天。
第四天,我走在一个旷无人烟的大坝子上。太阳已经靠在西山顶了,现出半天晚霞。我还是早上吃了东西,现在肚子里“咕噜咕噜”地直叫。我在小沟里掬了几口凉水喝,继续走,希望能看到一家农户,要点饭吃,在屋檐下蹲一宿,明天就可以到潮阳城。据老乡说,离潮阳城只有三四十里了。
太阳消失在群山的后面,时近黄昏,眼前是一个大湖沼,远远的山,平静的水被落日染得一片通红。转过一垄甘蔗地,见一个五十岁开外的放鸭的老汉正在把鸭群往竹棚里赶,一只小船泊在湖边,船上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正在淘米。看见他俩,我心里好像有些着落,就在湖边坐下来。等老汉将鸭群拢在竹篱笆内以后,才上前和他打招呼,向他说明我是二十军的,被打散了,想借住一宿。他听我说是二十军贺龙部队的,用善良的眼光上下打量我一番,大概见我还有学生的模样,问道:“你是读书人吧?”
“是呀,在军队里当文书。”我这样回答,既不暴露身份,又合他的臆想。
他点点头:“好嘛,你坐下来歇歇吧。”然后在临时垒的土灶前,一面加柴火,一面又对我说:“现在路很难走呀,土匪很多。”
“不瞒老伯说,我的钱全给抢光了,只剩一个光身人啦!”
他很同情我的遭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这个年头,你是过路人,有钱不要放在身上,埋在地里。在村里找上一家人,把一点钱给他,请他搭救你。等风声好一点,就把地下的钱挖出来,再拿一些谢过他,他就可以送你出去。不这样,你有钱命也难保。”他说得很友善。我相信这是他饱经风霜得来的经验。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