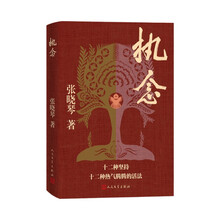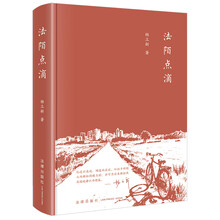从根本上说,自由是个体的自由,我们说的政治自由,其实也都在于赋予并维护个人的自由。在西欧,自由是一个近代的概念,在中国则是五四时代的概念。只有到了五四,中国文学才有了新的观念,新的主题,新的形式和风格。其中,散文的成就尤为突出。《新青年》首开“随感录”专栏,所载散文已大异于《论语》、朱子之类的语录体,而带有尼采的风味了。为向古文家示威,一代作家各自实验“娓语体”,于是有了蒙田武、培根式、兰姆式。至于那些人道的、同情或鼓动的、礼赞劳工神圣的文字,那些讽刺的、愤怒的、对抗权力的文字,显然为故家的文苑所蔑有。他们在打倒偶像、个性解放的历史罅缝间尽量地表现自己、施展自己,在五四以后的头十年里,就产生了一批个性各异的经典性文本,创造力的爆发是惊人的。
创造是自由的创造。任何有创造力的事物,都是通过对现存轨范的反叛和破坏以显示其蓬勃的生命的。文学也如此。如果作品失去了个性,作者是不存在的;如果整个时代的文学是均等的,雷同的,没有冲突也没有变化可言的话,那么,即使队伍十分宏大,一样可以视同无物。没有自由的文学,禁锢的文学,其命运注定是萎顿的,凝滞的,惟见墓室般的死气沉沉。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以及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格局。但是,无庸讳言,这其中包括对政治目的性以及工农题材的至上主义的强调,相应的对语言风格的规定等等,由于制度性措施的介入,也在不同的程度上损害了作家的艺术个性。及至文革时期,事情有了恶性的发展,致使数亿人民只有一个作家八个戏,几乎消灭了散文。三十年过后,危机依然存在,最大的威胁是语言的不纯。散文语言是自由的,个性化的,由于来自生命的丛莽深处,带有几分神秘与朦胧是可能的;又因为流经心灵,所以会形成一定的调式,有一种气息,一种调子,一种意味涵蕴其中。即从这所谓“文学的第一要素”而言,五四散文也是具有范式的意义的。然而,当代散文写作使用的语言,则普遍是宣传的、流行的、大众的、简易的、乏味的语言,是多次政治运动冲荡过后留下的,而又失去应有的人文教育和审美教育的修复的语言,是缺乏丰富个性和人性润泽的语言,刚性的语言,布满沙砾的语言。要建设一代散文,必先恢复精神的自由,具体一点说,必先从拯救文学化、人性化、个性化的语言开始。净化语言,这是最根本的工作,也是最艰难的工作。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