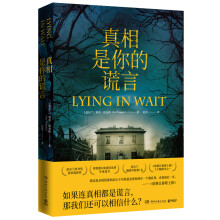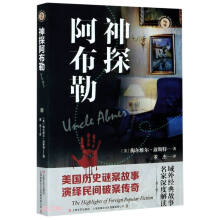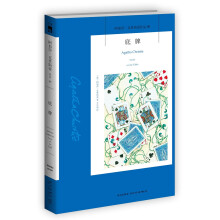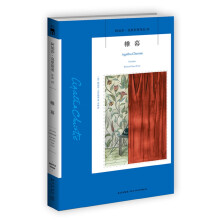《春秋》以微言大义的史家笔法开创了中国史学的绵绵传统,它不仅成了各类史书的“楷模”,还荣获了“六经之首”的殊荣。其虔诚的追随者《左氏春秋传》(《左传》)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姿态诠释了这种“一字之褒贬”的春秋精神。《左传·宣公二年》记录了一段引人无限唏嘘感叹的事件。晋灵公的昏庸与凶残使得国将不国,在明哲保身、忍气吞声的人群中突然杀出“一匹黑马”——谏臣赵盾。他直言不讳,冒死上谏,希望晋灵公“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可是换来的却是晋灵公发疯似的敌视与精心策划的谋杀。赵盾在忠臣义士的鼎力相助下虎口逃生,踏上了艰辛的流亡之路。对国家的深深眷恋和赤子情怀羁绊住他前行的脚步,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折磨着他那颗赤诚似火的心。在赵盾进退两难、备受煎熬时,他的兄弟赵穿在桃园大快人心地结果了晋灵公的性命。不久赵盾被迎回国都,却背上了“弑君”的千古恶名。在史官董狐面前,他据理力争,义正词严,但一切早已注定覆水难收。董狐振振有词地说:在晋灵公遇害时赵盾并没有逃亡出境,回来后又没有声讨杀害国君的赵穿,这就是“弑君”之罪。正大光明如董狐,为什么如此不通情理、不辨是非?孔子的解释很出乎意料,他说,董狐是少有的优秀史官,而赵盾又是极其难得的贤臣,两人的冲突无法评判,解决这一纷争的办法或许只有:如果一切没有发生,或者当时赵盾逃亡出境,一走了之。读来,着实让人一头雾水,却又是千真万确、名正言顺。这就是古代的“君臣”之礼,这就是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权威。董狐如是,孔子如是,整个中国历史如是,《三国演义》“帝蜀寇魏”的正统观亦复如是。
在今天看来,所谓“正统”,其实质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社会统治地位的思想”,不仅统治着社会物质生产,也统治着社会精神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懂得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历史上那些英明决断、功高盖主的臣子不敢随随便便“篡逆”,周文王尽管“三分天下有其二”,还要照样恭恭敬敬、战战競競地侍奉积贫积弱、腐败不堪的殷王朝。如果有谁敢擅自采取过火的行径,冒天下之大不韪,就会激起众怒,遗臭万年!“帝蜀寇魏”是《三国演义》的一条中轴线,也是《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倾向,理所当然成为我们欣赏、认识作品的一把钥匙。
遥想东汉末年的众多诸侯,莫不如此。受到黄巾农民起义的重创,汉王朝早已分崩离析、风雨飘摇,却打肿了脸充胖子,硬撑着正统的“汉家天下”。《三国演义》中袁绍、曹操等割据一方、拥兵自重、野心勃勃的“大腕”军阀,窥视神器已久,却拘于正统秩序的束缚不敢轻举妄动;退而求其次,不得不韬光养晦,采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缓兵之计,由此正统的威慑力可见一斑。董卓的一时冲动换来“天诛地灭”的惩罚;一世神武的曹操,直到死也没敢提皇位半个字,一心想用“分香”的遗嘱来澄清“篡逆”的传闻。但曹操的狼子野心路人皆知,就算他百般掩饰也逃脱不了历史与道德的审判。在“帝蜀寇魏”正统观的笼罩下,曹操终究免不了“汉贼”的罪名,终究免不了“白脸奸臣”的宿命。不过,回眸历史,可知“帝蜀寇魏”这一正统观念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更不是一蹴而就,它跋涉了曲折、艰辛的“旅程”,伴着非难与否定一路走来,最终在《三国演义》中“安居乐业”,发扬光大。稍作回首,历史的踪迹和思想的线索隐约可见,此段“公案”的前前后后也将一一揭开。
长话短说,还是从《三国演义》的来历谈起吧。作为历史演义小说,它再现了从东汉末年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到三分归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是对《三国志》等历史著作另辟蹊径的通俗化演义,可谓“七分史实,三分虚构”(章学诚语),所以主要人物都是“根红苗正”,主要事件则是“事事有来历”。同时,从宋、元之际的说书话本如《全相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到明代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再到清康熙年间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它经历了近400年的演说、流布;如果再往前追溯则可以推至唐代:“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李商隐《骄儿诗》),甚至可推至于三国稍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诸葛亮逝世后,蜀汉及中原建有多处武侯祠,流行不少传说),具有长达上千年之久的历史。在漫长的流布过程中,不断凝结、吸取了许多民间的思想和道德观念。这大致可以解释《三国演义》在老百姓中为什么一直那么“火爆”并持久流行的原因。鲁迅曾概括说,一部《三国演义》“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行‘史官’及‘后人诗’”(《中国小说史略》)。看来,“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是历史与民间相结合的产物,是主流意识形态(正史)与百姓草根意识“同谋”的结果,是一次历史与道德“亲密碰撞”后的文化积淀。
“帝蜀寇魏”的“三起三落”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先从正史去看个究竟,“帝蜀寇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着离奇、曲折的身世经历。套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它是经历了正反合的发展过程,择其要者,经历了以下两次变化:一次是从西晋陈寿《三国志》到东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一次是从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到南宋朱熹《通鉴纲目》。逝去的历史总会在后人的记述中留下斑斑痕迹,如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拥刘反曹’(即帝蜀寇魏)倾向的形成,有比较长远、复杂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从史学传统来看,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尊魏为正统,到东晋偏安江左以后,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就改蜀汉为正统。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沿陈寿先例,尊魏为正统,到南宋偏安以后,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一反司马光的看法,仍尊蜀汉为正统。”这里已经初步勾勒出了“帝蜀寇魏”形成的大体轮廓,让我们走近这鲜为人知的起落沉浮,揭开朦胧、神秘的面纱,看清历史必然性的真容颜。
西晋时的《三国志》开“拥曹反刘”风气之先,它遵循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例,以魏、蜀、吴独立记载,三书共65卷,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内容上魏国占了大半,与蜀、吴两国的总和平分秋色。开篇就十分醒目地设有武帝纪、文帝纪,而对蜀、吴则直呼“先主传”、“后主传”、“孙破虏讨逆传”等,从篇幅到层次均非对称,足见陈寿的立场与偏爱,尊曹抑刘的倾向十分明显。特别是把《武帝纪》和《先主传》两相对照,其明朗的褒贬用意立刻浮出水面。
虽然《武帝纪》揭了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老底,却在传后高度肯定他说:“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先抑后扬,贬中带褒,对曹操的崇敬、称赞之情呼之欲出。《先主传》却把“大耳”刘备放在刘焉、刘璋之后;白纸黑字地大书特书其“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一副出身微贱、人品低劣的“市侩相”跃然纸上。传末虽然评价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但又赤裸裸地直戳他的脊梁骨,说他“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其中“寓褒贬、别美恶”的春秋笔法隐约可见,两人才识、功绩的高下顿时一目了然。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