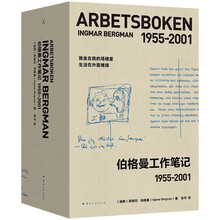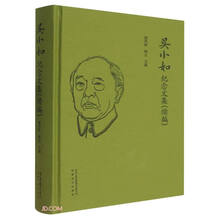二次赴朝日记
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至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
我第一次入朝,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后的一九五。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这次入朝只记了些访问笔记,未记日记。这里的日记系二次入朝的记事。自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的一月。
一九五二年
六月四日
夜十一时由京乘车赴朝。秋华送别。她在人们面前似乎很不好意思向我招手,可终于向我招了招手,然后跑去了。
我坐在车窗前,凉风吹着,我一直想了几个小时,我竭力使自己了解这一次行动的意义,增加我这次行动的力量。我想着,我这是带着许许多多人们的愿望,真挚而热诚的瞩望去的,我是去参加作战,用我的笔参加作战去的。我兴奋而又严肃。很晚才睡了一下。
六月五日
下午二时到达沈阳。趁空和谷世范同去看了电影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又引起自己对这位非凡的作家的景慕。夜深,至东北招待所,房间异常漂亮,真使人想住下去,但我知道此行是带了多少人的愿望,仍决定第二天走。
六月六日
遇蔡顺利部长所率的政工实习团。早晨到后勤办手续,他们很费心地帮我考虑如何走。有两个女同志拿出小本子让我给她们签字。于是使我想到,今后应如何去帮助她们。“她的成长”这个标题忽然闪到我脑子里。
晚和叶部长等一起出发。
六月七日
晨抵安东,住锦江山,与蔡部长所率实习团又相遇。锦江山风景宜人,绿树鸟鸣,与远方游玩了一趟,登上一块高石,遥望南岸朝鲜,虽然高射炮不断,但儿童们自由快乐地游玩。使人更易了解朝鲜战争的意义。
天色微阴,蔡部长决定提前出发。十时,汽车开动。到郊外野餐,他又动员了一回。坐上车继续走,看到一个岔路,插了一个牌子:“由此路开往朝鲜”。不断地看见小孩子,望见我们的汽车,就扬起小手。其中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也立在门口向我们扬手。大家很感动。十二点五十分跨过鸭绿江。水平而静。
过江后,即不断地看见穿白衣的朝鲜人,赤脚在田里插秧除草,小孩子在水里摸鱼,在学校的门口玩,妇女顶着东西,在路上行走。一路水明山幽,稻田水光倒映着山影,树林茂密,村头的垂柳,房舍的东方风味,引人人胜。
中午,在一户农家休息。小孩的腿上有伤,房东女人说,是美国“边机”打的。接着她告诉我们,这里昨天打下了一架美机。朝鲜人刚一接触,是不容易看到他们的热情的,可是只消相处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热情了。老妈妈的两个儿子参加了人民军,大儿子牺牲了,还有一个活着。老妈妈垂着一只膀子,在我们跟前静静地坐着。她摸了摸干枯的眼睛,并没有掉眼泪。在这静静的目光中掩藏着一种看不见的,但是可以感觉到的抵抗灾难的强大力量。
我和远方在房里休息,房东的姑娘穿着一件粉红上衣,一条黑裤子,坐在我们身边,语言不通,她拿了铅笔和小本子和我们笔谈。她告诉我们她是平壤特别市的人民学校的教员。她看我嫌炕热,把她家的被子给我铺上。还掏出一个身份证一类的东西给我们看,她二十二岁。她几乎不愿向我们谈什么灾难方面的事情。后来甚至不愿离开我们了,给我们写了她的地址,叫我们回来到她那里去。临走时,她又帮我们拿东西送行。我想和她握手,但没有握。
下午四时,汽车又开动了。目的地只离我们有六十里。山路更窄,但公路修得很好,两边的树几乎要接在一起。在绿阴下大家谈笑。这一车人都是干部,有一两个年轻人特别活跃。一个政治干部,他特别爱发议论,唯恐别人对当前的现实不懂或了解得不正确。在村子里时,他给房东一些罐头和饼干,又给大家解释,在北京下饭馆,一次多找了六百元,他马上送还了掌柜,当时整个屋子里的客人都用惊奇钦佩的眼光看他。他说:花六百元就买了个好影响。现在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了解我们,很需要让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切身体验。和他开玩笑的对手说:“那么,你给我一千元,叫我对你有个好影响吧,这是应该的,并不是用钱买的!”说得大家都笑了。他的对手是个天真的人,老爱在他的周围发现可笑的东西。他本来已经哈欠不断,但他一看到人们打盹的可笑的样子,马上自己哈哈地笑起来了,笑得也不困了。
黄昏,到了目的地,志愿军总部。房子都东倒西歪,屋里散乱。可是街上却有些热闹。还有中国和平理发馆、中华料理食堂等。朝鲜女人也穿得很整齐地在街上走。这里的工厂遭到部分的破坏,变压器、铁轮子在一边扔着,矿石的斗子在空中的高架线上停着。
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大矿洞里。洞子里还流着水,岩石上潮得也向下滴水。但挨着一边,却钉起了木板房间,亮着电灯,还有很大的饭堂。吃过饭,小屋子挤满了人,蔡部长、叶部长、邱参谋长(邱蔚同志),还有王洁清。我上去和邱握手,大家就闲扯起来。邱问我第几次来,我说第二次来,他说,变化可太大了。接着,他就谈起这次战争的残酷性,说有的阵地落了几千发炮弹。战士修工事的木头,一支支接起来,可以到四川成都。现在战士一天不停地打着洞,敌我阵地最近处只有一百多米,双方阵前的尸体都没有办法弄下来。战士在洞里也没有灯,下来时是被担架抬着,看不见东西。我问起杨成武司令员,他说,杨司令员害了失眠症。见电灯一亮,脸就变了颜色。我问怎么得的失眠症,他讲,杨司令在上次战役中,打得很紧,最后一个团战斗力只剩一百多人,只好几个团编在一起,后备力量也只剩下两个营,杨讲,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用。他彻夜不眠,有时叫:邱蔚同志,我们要研究!那时陈仿仁不断来电话:“不行呀!”这样好几个团编在一起,守一个主要阵地,才克服了危机,从这以后杨就失眠了。
以后又扯起了许多人的情形。谈起了谁在“三反”中如何等情形。蔡问,你怎么样,邱说也没啥。以后邱谈起换班时,要求学习的事,又说,我什么时候当过参谋长呢,我干不了这个事。蔡说,参谋长还不是打仗吗?……他还是说老马不能拉火车。
叶部长是一个可爱的人,遇到可笑的事情,他就爽朗地笑一阵。不知为什么他爱拍腿,好像不断有蚊子爬上他的膝盖,拍了以后也毫不觉得疼。
王洁清,过去我听说过没见过,人称八大怪之一。谈起话毫无拘束,不知会说到哪里。他嘲笑中国妇女封建,说,她们不看我,我也不看她们。你看,她既不看我,我何必看她呢!……还说,你们做保卫工作的,就是心眼多等等。
不知不觉又到了十二点。他们性格的直爽明朗,又给了我一个鲜明的印象。
六月九日
到宣传部。同卓部长、李部长谈了谈。李在去年谈话很少看我,今年却有很大不同,蒙他特别优待,把眼光投到我脸上。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自己说了一句话,就马上笑一阵,这个笑,似乎是这些都好像不该说,而他说出了,他笑一阵来企求别人的原谅。
已订好初步计划,准备先到63军,然后到人民军,再到平壤,最后到后勤等单位。
晚上,也许由于过度疲劳,睡觉中,旧病复发,脑子奇痛。
六月十日
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大半日。住在一个矿工家里。老头子是个老矿工,现在病着。一个儿子还在矿上,还有老头子的几个小儿子和女儿。一家人夜里盖着一条破被滚在炕上,也有的赤着身子躺着。吃的是高粱面和绿树叶子混在一块的饼子。他们的日子多苦啊。
六月十一日
早晨,房东老太太一发现我起来(她像是专注意这件事),就给我端来一大盆热水。她一整天都赤着脚在山坡上劳动,一边还这样照看我。人民多么好,多么善良勤劳,可是美国野兽却要毁灭他们。
六月十二日
翻过山去参加政治工作会议。看到路扬和廖鼎琳,我和廖几乎拥抱起来了。虽然他是我的上级,但我们有亲密的友情。他朴素、老实、肯干,就是文化低些。西征绥远时,我的衣服少,他曾把他的粗布褂子给我。西征绥远,是我的工作经历中满意的一段。
今天听甘泗淇副政委的报告。他批判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提出反对政治工作的空喊主义,要给战士以尽可能好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上,他提出物质是决定精神的,战士每天守坑道直不起腰,见不到阳光,连烟也抽不上。而在精神生活上,领导只是不断地冷冷地批评。政治工作不合乎人情,不给人以温暖和安慰。今后一定要使战士快乐,使战士们乐于抗美援朝,乐于视死如归。他并且说:古来用字,多么气魄,如归,比如明天咱们的李部长要回去了,有什么可怕呢。说到这里,大家哄然大笑以后,他又谈第二个问题,就是建设支部工作。他叙述“三反”中有许多重大收获,为过去的政治工作所少见。许多领导干部的歪风,连上级也无法整的,这次都让支部整出来了。他盛赞支部的伟大力量,这力量可以克服一切。他说今后他不多抓,就抓这一个环节。整个讲话的精神,就是反对政治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贯彻爱党的观念。他讲话爱笑,两个鬓角深入,脑袋上只有一小撮头发。
讲话中陈赓将军不断地插话。甚至有时抢着讲起来,不知谁是主讲。他的鬓发也秃了,可是面色赤红,胡子浓黑,十分健康,扣子解开,露着怀。他像一匹没有受过拘束的骏马。说话热烈、尖刻、俏皮,他的补充把内容强调得非常明确肯定,不容怀疑,而且丰富多彩。他的话,总使听众大笑。当甘主任讲到后勤某首长处理一件恋爱事件异常过分时,陈赓立刻插话说:“就他一个人长着鸡巴,别人都没有长着鸡巴!”使得会场上大笑不止。虽然如此,但透过这一切,使人深感他的嫉恶如仇和维护真理的热烈精神。这个人一直到他胡子变白,也变不了这个性格。
晚上看过电影与黎娜同归。她,很热情,有着女同志可贵的东西。
六月十三日
见普金。他是我少年时抗大的同学,一块上前线的,他的恋爱史和愿望都给我讲过。现在他是志愿军新华分社的社长了。他几次三番让我给他的记者们介绍经验。
在他那里喝了一点酒,就过山去找苑星。在山坳坳里听见朝鲜小孩子念书的声音,乍看看不见,仔细寻找,三三两两,有在大石头后边的,有在布篷子外边的。他们拿着油印的课本,赤着脚在那里读、背诵。小女孩子也是这样。我又到一个小石洞里,她们穿着很脏的小白裙子,坐在地下,小胶皮鞋子放在一边,用整整齐齐的声音念着。我叫她们唱歌,她们就唱。她们会唱五六个中国歌。正中墙壁上,中间是朝鲜的国徽,一边是斯大林的像,一边是毛主席的像。这都是用血换来的呀!
放学了,我和她们一起走。她们回去吃点菜饼子,就又来学习,她们度着艰苦的日子!
到了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和几个军及兵团的作战处长都见到了。
和苑星谈了约两小时,他对我很客气。他曾在189师当参谋长,他说他和师长蔡长元有两次几乎被炸弹炸伤。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北平郊外和傅作义军队谈判中他谈得很好。他现在是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长。
晚上看20军文工团演出。在一个地下的石洞里,舞台用红丝绸幕布搭成,给人以很愉快的感觉。演出十一个小节目。还有几个战士的节目,具有浓厚的战斗色彩与生活色彩,很受大家欢迎。有一个剧描写战士打石头,把石头拟人化,宣称谁也动不了他,志愿军战士要想动他不过是妄想。有两个志愿军战士想了很多办法都弄不动他,最后终于战胜了他。这剧有相当的艺术性。另外,有一个炊事员自编自唱的炊事员四季调,传达了他们愉快的心情。另外,还有对唱快板《化学炮与昆明造》,把炮与炮弹人格化,也传达了炮兵战士的心情。还有《小小军工厂》表达了战士打铁制造工具,解决困难的决心。我几乎目不转睛看着我们战士的演出。文工团员们那么年轻,在激烈的火线上为战士服务,使我感动。他们战斗的风貌也给我以鼓舞。
全场都热烈赞美他们的节目,20军的主任坐在我们身边,乐得只是说:都很仓促!
夜与曹欣科长同归,并托曹把上面几个剧本给《解放军文艺》寄去。
六月十四日
上午,新华社记者编辑与《志愿军报》的人员召开座谈会,请我报告写作经验。我现在简直好像成了大人物,都对我这么尊重和客气,弄得我自己在人前很不自在。
我跟他们谈了真和假,细心和大胆,集中和提炼等几个问题,虽是我不成熟的艺术思想,但却是我的体验。
但他们又提出很多问题,主要是要我告诉他们一个什么秘诀。
下午,到作战处找林副处长谈,他很负责地把作战过程告诉了我。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作战处长,颇有朝气。
晚上六时,乘吉普车奔自己的老家——63军。在幽幽青山中行进。自己有名了,人家对自己的企望大了,派专车送。自己的创作,不知是否能和这些汽油,司机的劳动,大家的企望相称。
这一夜过了几道敌机封锁区。防空哨在黑夜中宛如战斗,枪声不绝。汽车灯光中能看到他们坚定的身影,小白旗很有力量地一指,汽车才能通过。
一路汽车特多。司机的眼最尖,夜色中不知他们凭什么一下就发现了熟悉的伙伴,一边亲热地招呼着,一边停下车,或者拉住手,或者互相亲热地踢对方一脚。然后送给对方一支烟,就又各自驾着车背道驰去了。每遇到对面有车来,汽车的大眼睛亮一亮,好像打招呼一样,然后变成黄色合上,显得亲热而有礼貌,引起我极大的兴致。
过栗里时,敌机封锁得紧,两辆车都开到桥上各不相让,车拥挤起来。山上是敌机打着的火,被飞机又扫了两梭子弹。后来终于未遇到什么危险才开过去。
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姓朴,是朝鲜族。他曾在四野工作,后回朝鲜。曾驾坦克打到釜山。
车未到新溪,天已大亮,才三时半。司机着急,就发了疯地开起来。
天越来越亮,太阳也快出来了,地形也不好,于是决定隐蔽。汽车拐入一个小村庄。这座小庄傍山,树木浓密,鸟声悦耳,朝鲜女人到井边汲水。几个朝鲜老人抱着小孩子在那儿抽烟,看见我们的吉普开来,都满脸堆着笑意。汽车隐蔽到他们这里,本来是有危险的,可是他们却这样乐意地笑着,使我感动。把车隐蔽好,一说找房子,一个男人马上就顺手指着他的房子。一个中年女人背着小孩,拿着瓢走来,给我们淘米做饭。她的孩子又黄又瘦,两只小手抱着母亲的背,嘴窝里眼窝里就有一疙瘩蝇子。哭的时候,母亲就伸过手去扫他一下。不一会儿,给我们做熟了饭,她就又去舂米。另一个强壮的中年妇人赤着很脏的脚坐在那里去拐磨。这是新近在村里借的麦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