咀嚼耻辱
第一节 耻辱的心灵
我居然至今还活着,活在这样的世间,而且活得如此平安。我并不为此庆幸,我只感到无限耻辱。
我曾经长期迷惑,不知道人究竟该为尊严活着,还是该为使命活着。我一直倾向于相信后者,像越王之卧薪尝胆,像司马迁之忍辱负重。后来我终于清醒,所谓忍辱负重乃是活命哲学的借口,是中国式的自欺欺人。且不说大多数人的所谓使命,根本就不含有合人性的高贵素质,倒多半是反人性的。即使是高贵的使命,又哪应成为生命的包袱。我们唯一至高无上的使命,不就是捍卫人的尊严么?我终于没有理由自欺,我终于认清人应该为尊严而生活。可是我们的尊严早就丧失殆尽,我们又不敢起而寻找尊严。我们分明是在苟且偷生。
既然不能为尊严而活,为什么不可以为尊严而死呢?
我却至今不死,我却至今还活在这样的世间,而且活得如此平安,似乎我们已经得到了尊严,似乎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
这是什么样的耻辱啊!
我们何止是没有尊严,我们实在是一无所有,可是我们却不敢正视。
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到连改变一无所有的权利都没有,可是我们却依然不敢正视。
我们事实上已经意识不到尊严的丧失,意识不到已经失去了改变一无所有的权利。我们已经没有了权利和尊严的意识,这是世界上最彻底最可悲的一无所有。在所有别的时代和别的区社,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一无所有。
我们像一条癞皮狗,怯生生地走在充满敌意的村巷里。我们对那些敌意已经毫无敌意了。我们一边怯生生地走,一边向村民们仰起头来,送去媚笑,摇着讨好的尾巴。当任何一位村民向我们跺脚或打石头,我们就夹着尾巴开溜,默默地开溜,没有愤怒,没有咆哮,只有几声惊恐不安的呻吟。
我们从东巷溜到西巷,从南巷溜到北巷。到处都是敌意,到处都是棍棒和石头。我们终于溜到了荒野。我们坐下来喘息,却依然没有愤怒,没有咆哮,没有敌意,更没有复仇的决心和行动,倒好像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只有一边舔着伤口,一边为免于一死而露出庆幸的笑容。
这是怎样丑陋的笑容啊!
可是我们一点也不懂得这是耻辱。我们已经完全没有灵魂,完全没有自我。我们因为没有自我和灵魂,所以也就没有了对于尊严的需要,没有了对于人的生活的需要。我们是没有需要的生灵,我们只需要一无所有,我们只配过一无所有的生活。
我们已经是非人,而且决不是从今天开始的。
我十分真诚地渴望改变这种一无所有的生活。可是我曾经付出过什么努力呢?采取过什么行动呢?
我们渴望着有民主,同样打算着一有民主我们就去参与。
我们渴望着有面包,同样打算着一有面包我们就去劳作。
我们渴望着有自由,同样打算着一有自由我们就去战斗。
可是我们却不懂得问一问自己,你不去参与,民主从何产生?你不去劳作,面包从何产生?你不去战斗,自由从何产生?难道真的要等待救世主把这一切布施给我们吗?
这一问问出了多少耻辱啊!
曾经有那么一位杭州姑娘,因为憎恶社会风气之污浊,跳进西湖,以命反抗。我却批评她没有反抗到点子上。
曾经有那么一位北京青年,为了民主赤膊上阵,拼力呐喊,因而身险囹圄,囚居于发霉的铁窗之下。我却批评他的理论不够力度。
曾经有那么一位中学毕业生,刚刚步入社会,惊慑于生活的丑陋,在幻灭中自杀身亡。我却批评她过于娇气,过于软弱。
可是,我自己呢?我有多少次幻灭的痛苦,可我却依然活着,而且活得这么平安。我蒙受过多少次非人的凌辱,可是我却全都忍受了,有时还以忍辱负重自欺。我的坚强在哪里?难道就因为我敢于苟且偷生,倒有了对他们评头品足的权利吗?
当窗前的茶山一天天披绿挂翠的时候,许多热血男女,正在一些重要的都市,以各种行动纪念中国仅有的一个伟大节日,为沉闷的生活创造一丝生机,不惜跪下高贵的膝盖,不惜冒着失去生命失去自由的风险。我却坐在这间斗室里,犹如困兽与世隔绝,写着这样一些苍白的文字。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没有正义,没有尊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没有了。只有耻辱!只有耻辱!
我犹如大梦初醒。我扭着自己的头发,睁着恐惧的眼睛自责自问——
我为什么曾经这样生活过?
我为什么依然这样生活着?
我还要这样生活下去吗?
耻辱的人啊,还要耻辱到什么时候呢?
应该正视我们的耻辱。
仅仅懂得苦难是不够的。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的因子。只有当我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苦难,才使得苦难无法把人吃掉,并且才可能使人得到超越和升华。
谁曾像阿Q和祥林嫂这样,承受过如此深重的苦难呢?但他们只能屈服于苦难,只会把苦难不但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而且作为一种心理素质,一代一代遗传下来。就因为他们没有耻辱感,没有对苦难的反思和反抗。
应该反抗苦难。
苦难总是由每一个受难者分别承担的。无论你怎样同情十字架上的基督,但那骨肉的灾难只能由他一个人独自承担。即使你以形而上的思考,体悟到了人的原初苦难,但你的体悟终究只是你个人的思想。你的肚子不可能代替别人来挨饿。只有耻辱感才可使人类沟通。每一个生命个体的苦难,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罪恶,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的丧失,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耻辱。那集中了人类一切优秀品质的基督,竟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他在十字架上的作恶者,竟然也是两脚动物,这不是我们共同的耻辱么?受难者因为受难而尊严受辱,作恶者因为作恶而尊严丧失,这全是我们共同的耻辱。
苦难是暗淡的,当我们用耻辱感将苦难转化为耻辱时,我们已经蕴含着反抗苦难反抗耻辱的光辉。
苦难可以属于人,也可以属于非人。而且,苦难的直接目的就是把人变成非人。
耻辱感却只能是属于人的。非人无论是怎样地耻辱,却绝对没有耻辱感。
我们在如此一无所有的生活中,竟然如此心平气和地忍受,这就证明着我们全都是非人。苦难在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取得了怎样辉煌的胜利,它已经把我们全都摧残成了非人。
非人的最可悲的特征,就是他不懂得追求真的人。
曾经有过那么一个非人,他对真的人怀着那样虔敬的心情。他那样真诚地反思着现实的丑恶,忏悔着自己的耻辱。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个由真的人组成的美好世界,那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充满了人的光辉。他立时那样地自卑,自羞,自惭,自愧。
他因为知道自己是非人而对真的人怀着恐惧。
他因为知道自己是非人而知道难见真的人。
他是鲁迅笔下的狂人。
狂人永远只能躲在房里翻弄古籍并让自己也成为古籍吗?
这种对于真的人的虔敬心哪里去了?这种对于自身非人状态的耻辱感哪里去了?
没有这种耻辱感和虔敬心,非人永远只能是非人。
我为自己是个非人而耻辱。
我为自己安守于非人的生活,而没有用生命捍卫人的尊严而百倍地耻辱。
我对自己最有力的惩罚就是要自己咀嚼这耻辱。
我渴望着在咀嚼耻辱的过程中,变得坚强一点,有勇气一点,与自己心中真的人的形象接近一点。
我知道自己成不了真的人,但是我依然要反叛自己。
我宁愿做一只被围猎的豺狼,而决不做一只癞皮狗。
我宁愿做一个魔鬼,而决不做一个安分守己的非人。
我相信别的非人们的耻辱,也不见得比我少。我愿所有的非人都跟我一起来咀嚼咀嚼,放下非人的自尊心,来咀嚼我们共同的耻辱。
怀着虔敬的心来咀嚼,带着对人的尊严的向往来咀嚼。
要长久地咀嚼。
咀嚼出苦味,咀嚼出恶心,咀嚼到难以忍受,一直咀嚼到要么就跳楼自杀,要么就起而反抗这种耻辱的生活。
第二节非人的宿命
像往常一样,我吃过晚饭就去了她那里,享度宁静的黄昏。小斤自然是以那种期待的目光,迎接我进房。在偌大一个校园里,只有在她那里我不感到压抑和恶心,不感到格格不入。因为她不像别人那样势利眼,不像别人那样庸俗而苍白,她不会把我看作一个昏昏沉沉疯疯癫癫的角色。在她那里我可以狂妄地,吹牛,可以轻松地幽默几句,可以把她的书一本本地扔过来扔过去,还可以在她床上横躺斜卧的,我可以享有一切自由。
她正在听一支乐曲,也许是莫扎特的吧,那么温婉甜柔。我取来一本鲁迅的书,歪在床上看《藤野先生》。记不清这是第几回读它。开始是漫不经心,后来进入了境界。藤野先生对于鲁迅的温暖的关怀,和鲁迅对于他的先生的深切尊敬和怀念,与那支温婉的乐曲一起,交织成柔美恬静的气氛。原来鲁迅是这样多情的人,他对人类怀有这样深广的爱心。我以前把他看作一个咬牙切齿的怒目金刚,显然是歪曲。有了这个领悟,鲁迅笔下的一切形象,和鲁迅自己的内心世界,立时在我眼前呈现出全新的内涵,或者说是深一层内涵。
小斤见我在读鲁迅,乃关掉录音机,给我讲她游历绍兴的见闻。她首先用轻松的口吻描述咸亨酒店的情景。我想象着那种阴森森的气氛,孔乙己拖着残腿沉重地走来,书生的尊严扫荡尽净,忍受着无边无际的嘲弄和戏侮。越咀嚼越感到阴暗寒冷。
人怎么被摧残到了这一步!
我一边这样暗自发问,一边又看见阿Q戴着破毡帽,唱着“手持钢鞭”走过来。他的细瘦辫子一摆一摆,刺得我眼睛酸一阵热一阵。我又模模糊糊看见祥林嫂,她的脚步是那么苍老疲乏,那嘎哒嘎哒的破竹竿声,诉说着世间的冷漠和悲惨。这些人原本都应该是可爱的人,他们之所以令人厌恶,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身,他们不再是人。我想到生活中那些挣扎着的人们,和一切不再挣扎的人们,我们每个人不都处在这样一个非人的深渊中么。
人为什么被摧残到了这一步!
我似乎要向谁质问,又无处质问。我的心强烈颤动起来。
,“不行了,我好想哭。”我把书一扔,猛一翻身,小斤趁势把我搂住,搂得紧紧。我像寻找安慰似的,也紧紧搂住她。孔乙己、祥林嫂,还有我们的现实,以及现实中一切丑陋的人们,都一步一步地,齐刷刷地向我压来。我的身子抖颤起来,喉头也跟着抖颤,终于压抑不住地哭出声来。但是不流泪,只是干泣,脸部和其他部位都变形到最大限度的干泣。
我以前竟然只知道厌恶和批判阿Q们,而不是首先爱他们。我因了这一点而十分羞愧。鲁迅在写作它们时,难道只是厌恶吗?他以那么强的人的意识,那么深广的爱心,会怎样地因这些非人而痛苦。他是否常常念叨人为什么被摧残到这一步呢。
整个世界因为人的丧失而一片阴暗,所有的人都因为已经丧失了自己而无力感知黑暗,于是所有的黑暗凝结成一块魔石沉沉地压在那个矮矮的绍兴人心上。我躺在小斤的臂弯里,体味着鲁迅当年所可能体味到的一切苍凉和痛苦。
我的脸部又像水波一样被扭曲被变形,身子又跟着微微发抖。我把脸埋在小斤的臂弯里,无所适从地蹭来蹭去。
打开录音机,打开录音机!
怎么呢?让它吵一阵,吵一阵。
但是,那温婉的乐曲无法安平我的心,我依然处于莫名其妙的紧张状态。小斤继续讲绍兴见闻,而且提高声音,想以此缓解我的情绪。“我们还去看了秋瑾墓,和那个什么亭。”
“来轩亭,秋瑾献身的地方。”我声音短促地补充。
原来我总以为,秋瑾在事发以后,坚持不逃走,是个错误。可是今天想来,她的献身也带着一种自我毁灭的欲求的。在那样黑暗的年代,离光明是那样遥遥无期,哪一个觉醒者能受得起这样长久这样沉重的绝望呢。我忽然看见华小栓在刑场边等着啜饮秋瑾的血,看见阿Q在骂秋瑾犯上作乱罪该万死。那苦难深重而又冷漠残酷的人啊!
反抗的生命被扼杀了,像秋瑾,不反抗的生命也被扼杀了——所有阿Q们不都是没有灵性的行尸走肉么。那些生存着的觉醒者,要么被摧残成疯子、狂人,要么就要为一切反抗者和不反抗者体味着所有的痛苦和耻辱,这是何等深广的苦难!鲁迅心灵所受到的摧残,难道比秋瑾们和阿Q们和狂人们小一点么?那么老人所承担的乃是所有摧残的总和。
我深深觉摼出生为一个中国人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前面已无路可走,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无限的耻辱,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在浓缩,以巨大的速度向某个点浓缩,所有天体都带着轰然巨响朝这一点狂奔,而这一点正是我的脑袋。我感到头皮发麻,脸上肌肉发胀。我抬起右手,在脸上烦乱地极快速地挥动摩挲,似乎是抹泪,然而并没有泪。配合着手的挥动,我把头摇得飞快,快得有飘飘忽忽的失重感,似乎这样就可摆脱那从四面八方狂奔而来的压力。
小斤已经知道,无论是她的话还是录音机的乐曲,都无法驱走我心中的痛苦。她于是关了录音机,深情地爱抚我的脸,那柔嫩的手指,传导着她的怜惜与忧虑。
“你呀,你真要发疯了!”
平时也有人骂我疯子,我从来引以为骄傲。可小斤说这个“发疯”,显然别有含义。想到自己也许真的已经不正常了。我突然出现了两秒钟的平静。我静止不动,睁开眼睛,向虚无境界寻找一道白光,那道白光是刚刚从我意识深处闪出的疑问——
怎么?我已经是非人么?刚刚体味到被摧残的痛苦,就已经是非人了么?连挣扎的余地都没有吗?
仅仅两秒钟的平静,身子马上又剧烈抽搐起来。小斤紧紧搂住我,像要做我的保护神。我的哭声在她怀抱里盘旋一阵,随即充满在房里。黄昏在房里颤抖而且倾覆。所有轰然作响的天体终于同时撞击在我的脑袋上。我真切地感到了灭亡的痛苦,我十分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肉屑四处飞迸。我无可挣扎地坠向耻辱的深渊。
在我坠向深渊时,似乎有一阵温暖的风,柔柔地将我托住。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小斤的怀抱里。她正怜惜地望着我,温暖的泪水一串串流下,轻洒在我的干枯而又苍白的脸上。
这些年来,有多少次罪恶的力量,将我的心砸碎一次又一次。有多少次,我像那个颤抖的黄昏那样,绝望地干泣。那个黄昏,是我今生的第一次死亡,同时也是我的第二次新生。当我认清了自己是非人的宿命,后来倒是更加坚强些,虽然同时也多了一些苍凉。
我常常庆幸那个死亡的一刻,有她给我以深情的抚慰,在我干涸无泪时,她又以温柔的泪水,濡润我的新生。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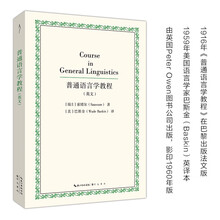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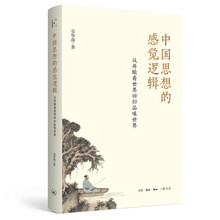



——《描述耻辱-咀嚼耻辱》
在血雨腥风的时代,我们会因为宣诉了个人的悲愤与抗议而表达出族类深心的真情与理想,在天崩地裂的时刻,我们会因为多担了一份族类的患难而成全了个人的光荣与永恒。诗人雪莱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竖琴,要为宇宙奏出痛苦和忧伤。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不正应该是自己族类的竖琴吗?
——《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的奴隶体验》
圣人易于受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戴,易于取得现实的成功,他们往往在其有生之年就轰轰烈烈,功成名就,甚或高居万人之上,权重一世,俨然教主模样。而英雄则是上帝派给人类的先知,他感觉灵敏,眼界高远,能够深切理解隐伏在最深层的人性的需要和历史的需要。或者他虽不甚理解。却能以自己的天性来感觉它们,表现它们,他们很难与大众一拍即合。
——《寻找精神资源·重温英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