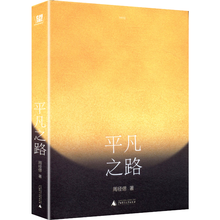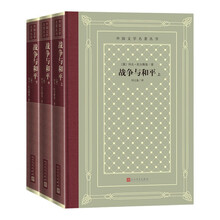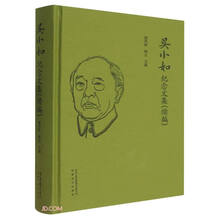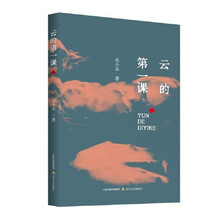五年前,也许更早一些,有一个鸽子般的少女坐在开满了鸽子花的山坡上,独自一人默默咀嚼一颗小小的山楂果。这果子对于她来说,也许熟得早了点,难免有些儿酸,有些儿涩,甚至有些儿苦,虽然其中也不乏那固有的甜味。她咬碎了它,一种独特的、微妙的情绪便弥漫于她的心中,而当它流溢出来时,就变成了诗。<br> 这就是胡鸿和她《初恋的情绪》。<br> 初恋的情绪,对于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来说,原本应该是极甜蜜极温馨的。林问之散步,花前之流连,春光明媚中之凝视,月色朦胧中之亲吻,不是许许多多少男少女都在编织这样一个梦,许许多多诗人都在把这梦做成蜜饯,送给那些爱吃甜食的孩子吗?<br> 然而胡鸿却不。<br> 胡鸿“初恋的情绪”,几乎一开始就是“不安和甜蜜混杂在一起”的,以至于当其骤然降临时,她一下子不知所措,“一声不响坐在那里,只想哭”。尽管从此以后,“河边鸟声开放了柳树,三月的黄昏真暖真甜”;尽管从此以后,“因你的到来我的小诗,在桂花浓浓的相思里聚满阳光”。但是,她也同时清楚地意识到,从此,“夕阳的垅上”之所生长,绝不只是欢乐,更多的将是忧伤。她甚至感到“一种恐怖感从残月里阵阵涌来”,而且“任我在风中怎么奔跑也吹不散”。终于,“我潮湿的步履再也不能沉重地走向你”,“黑暗中我咬碎了山楂果我的心”,只剩下那条“哭紫的路”,“淋着歪歪斜斜的苦痛”。<br> 唉,这过早地被秋风吹落的山楂果啊!<br> 暝,这苦涩而又酸甜的初恋的情绪啊!<br> 奇怪,小小的年纪,哪来那么多的忧伤呢?初恋的情绪,哪来那么多的苦涩呢?少女的心头,哪来那么沉重的十字架呢?莫非这一切,不过“为赋新诗强说愁”?<br> 并非如此。<br> 其实,只要稍加体察就不难发现,“初恋的情绪”一开始就是朦胧的、想象的、不确定和非现实的。“不知道是哪个没有风没有雨的黄昏,我开始忧郁地爱你”;“田野油菜花金黄地铺向我,我拿着写给你的小诗不知怎么办”。终于,“在想象中你朦朦胧胧地走近我.用自信和幽默把我围猎”;而那个“我”,却“只能站起来,摸摸没有了蝴蝶结的童年愣了又愣”。这一切都来得太快也太容易:“像你认真地学英语单词那样,认真地窥破了我的秘密”;她有着太多的准备又毫无准备:“我还没看完那本格林童话,就这样你走进了我的门”。她不得不承认:“这个季节是你的足音一夜间叩开的”。“你金色的莽原之风没遮没拦,深深淹没了我的渴望我的爱情”。<br> 显然,这种爱的方式注定了这种爱一开始就是悲剧性的。这是它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强烈的忧伤抑郁情调的根本原因。因为爱情从来就不是单方面的爱慕与追求,它是一种必须有回声的灵魂的呼唤。也就是说,爱情必须是“对等”的:同样的渴望,同样的爱慕,同样得到回爱。但在《初恋的情绪》中,恋爱双方的感觉却不对等。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现实价值”不相等。也许在旁人看来,她和他正所谓“天设一对,地造一双”,或者他比她差得远,根本不值得她去爱。但是,在爱情中,并没有什么“现实价值”,只有“感觉价值”。只要一方觉得不等值,它就是不等值的。而我们读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感觉,一种一方以“压倒优势”征服另一方的体验:“海潮般你淹没了我的朝夕,浩浩荡荡用你男子汉的气势涤荡了我”;“为什么我总在你面前说不出一句话,不能完成我的整个形象呢”?“最惊心的是你远去的足音,笔直地抽红了我呆滞的眼睛”,“我的眼泪和渴望在海水里默默奔流,而我不敢升起那张神秘的白帆”。这种在对象那里完全丧失自我的爱情,难道不注定了要以悲剧告终吗?<br> 然而《初恋的情绪》的意义也正在于此。这“初恋的情绪”是胡鸿的还是别人的,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也许是无意中)描绘了新一代女性在这变革时代的微妙心理:一方面似乎是觉醒了自我意识,义无反顾地要去寻找自己心中的“男子汉”;另一方面,却时刻准备着,一旦找到,就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让他“那样专制地使我幸福”。在“挺起你健美的角肌,让我栖息少女的幻想”的向往中,在“我独自走在你北方的阵雨中,等待心的辙痕跨过思念的静谧”的期待中,在“你葡萄般酸甜的眼睛闪闪烁烁,我竞一句话说不出”的被征服的幸福感中,我们看到的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吗?从宗法礼教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新女性,却又因“寻找男子汉”理想的设立再度丧失了自我,这真是何其不幸乃尔!为什么她们就不能想一想,“男子汉”们是否也该有同样的“献身精神”呢?她们难道不该使自己也变成“强有力的”(当然是心理意义上而非生理意义上的),从而问心无愧地和完全对等地接受对方的寻找和选择吗?倘能如此,则真正的、本来意义上的爱情,就会来到我们中间。<br> 这需要时间,但并非对于一切人都是漫长的。我们高兴地看到,在经历了一番凄风苦雨的阵痛之后,鸽子般的少女已经长大成人。尽管“没有人能遗忘她的初恋,也没有人能遗忘失恋带来的痛苦”,但恰恰是痛苦而不是其他,使她变得刚强和成熟起来。人类永远追求幸福,这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如果没有痛苦,人类又会在幸福的甜腻中沉沦。这是历史悲剧性的“二律背反”。因此,痛苦较之甜蜜,忧伤较之欢乐,有着更为深刻的美学意义。事实上,正是在经历了痛苦之后,胡鸿才写得出这样刻骨铭心的诗句来:<br> 你走吧我恨你<br> 为什么<br> 你只用日出的晨雾<br> 淹没我所有思念的山谷<br> 也正是因为在痛苦中升华出自我意识,她才有权利也有力量宣布:<br> 让风让雨都吹进我的小窗吧<br> 淋湿每缕发瀑颤栗的忧伤<br> 山楂树倒下的时刻<br> 我不再畏惧暴风雨的来临<br> 这正是独立人格的开始确立。不再是困惑于“为什么你我都不可能径直走进夏天”,而是坦然宣布“你我会告别心灵的沼泽,走向远方”。如果说,他们的相爱是不对等的话,那么,他们的分手就是完全平等的了。从此,她将不再作为一只受伤的鸽子,而是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去寻找真正的爱。<br> 即便如此,这些小诗无论对于她还是我们,都仍然具有美学上的意义。因为那里有她的追求。尽管“不是一切爱都能理解”,“不是一切的爱情都有回声”,但对理解和回声的渴望则是一切爱情都有的。也许,正因为有渴望而无回声,那爱情才忧伤,也才因其忧伤而美丽?那么,当“初恋之旅在泪中完成”,当“一段弦上的夏日凝固在子夜的山楂果里”时,那渴望和追求,难道不该更为凝重地留在了心底吗?<br> 在这里,初恋的情绪终结了,但追求与渴望却永在。我希望它永在,也相信它永在。因为正是有了它,生命才永在,世界才永在,人类才永在。<br> 当然,诗和艺术也永在。<br> 注:本文原载1988年第3期《芳草》,有修改。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