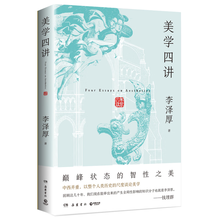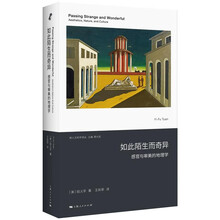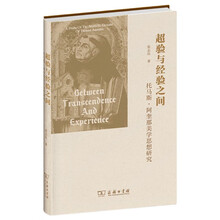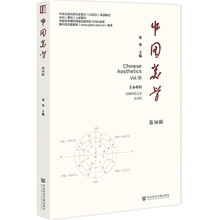中国上古史官源自黄帝,后世传统规范成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严格职能。宇宙和人世间的一切变化,都汇聚于左右史之实录中。其次,中国上古史官一身三任,既为统治者(首领),又为巫师(通天人一体者),又为客观记载的史官,“经验-思考-观念”萃于一身,以待独创之具形。“盖史官者,经验之府,观念之所从出也。由五典五悖(载长老言行),至五礼五服五刑,即明由史官所见之观念形态,自始即为一道德政治的形态,紧系于集团实践而生出者。而如此所引生之观念,又必切于人而通于天,故于典日天叙,于礼日天秩,于服日天命,于刑日天讨。凡范围实际活动的规矩典则,皆直接由道德政治的集团实践中而予以理性的根据,故皆日天,即宋儒所谓天理也(注意:古之根据于‘理’者,即日根据于天——引者注)。亦即可于此而直接透视-道德的理性实体。而此实体又不远乎人。故于聪明虽日天,而又日‘自我民聪明’,于明威虽日天,而亦日‘自我民明威’。”牟先生之结语是:“就史官之职掌所确定之观念形态,可以‘掌官书以赞治,正岁年以叙事’两语括之,而此两语之大义,即为‘本天叙以定伦常(德),法天时以行政事(智)’。”①中华民族精神观念之“定伦常”/“行政事”,均是“本天叙”与“法天时”(即“德/智”之源),这是中华民族之“天人一体”观念发生之总源头。括而言之,这就是由上古史官依据集团实践方式,所凝定了的“观念之具形”。牟氏的“观念之具形”论,是黑格尔“理性实体”(即精神实践)与亚里士多德“形式”因在中华民族精神观念之集团实践中,走向“一本万殊”之理论创造。
概而言之,中华民族精神观念在原始阶段之“具形”,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精神、意识之阈限为对峙性的“天人一体”之高远境界,二是精神、意识之动力契机是本善向上之道德仁心。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