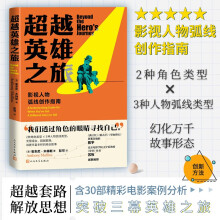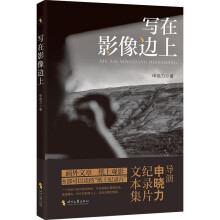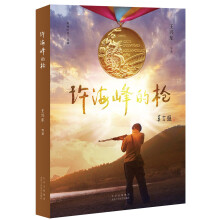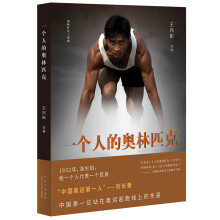九龙驹悲歌
在取经路上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他是西海龙王三太子的化身,是唐僧的第四个徒弟:白马。
从《除妖乌鸡国》、《偷吃人参果》、《祸起观音院》,到《三打白骨精》,我们都没有一匹自己的白马。原想养马很麻烦,不如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找马,但是这给我们增加了很大困难:例如在海南岛拍摄时,找不到白马,剧务好不容易才借到一匹很漂亮的棕色大马。美工师用大白把它浑身涂满,看上去还能凑合。但这马被刷上颜色后,猛然乱蹦乱跳起来,挣开了束缚,一直跳到水田里去!这下可糟啦,它身上的颜料一沾水,就都掉了色,成了一匹花马!而且它提高了警惕,人们休想再靠近它,根本不可能给它补颜色!我们只好给他们师徒拍个远景,走个过场算了!
更可笑的是在湖南张家界。打前站的李诚儒报告说,那里根本没有马,更别说白马了!我叫他继续找。可是我们到了张家界,已经开始拍摄了,白马还没有找到。我给了外号“王铁嘴儿”的副导演王小颖一个任务:不管在哪里,三天内找到白马!王小颖想尽办法,急得嘴里起了燎泡,可是连湖南的周边都没有!后来他在火车上听说湖北与湖南交界处有白马,于是他就奔了湖北。
三天内,王小颖在电话里告诉我:
“这里有一匹白马,可以借给我们,但主人要跟来,要多少多少钱。”
我说:“什么条件也不要讲!拉回来就是!”
白马果然按时来了。大家一看,傻眼了!这马又矮又瘦,皮包骨头,还总是低垂着头,似乎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哪里有一点儿白龙马的气势!
我问它的主人:“它怎么这么瘦?不是有病吧?”
他说:“是赶路赶的!”
不管怎样,总算有了马,而且是白的,这就不错了!但是一到拍戏,又有问题了。汪粤一上马,脚就踩到了地上,这小马歪歪咧咧地直要倒!我说:“算了,别骑了,就拉着吧!”
所以在《三打白骨精》这集戏里,唐僧就没有骑过马。我们拍摄时也尽量避开全景,免得人和马比例失调。唐僧师徒上山的戏,我准备只上一次黄狮寨,让师徒四人化上妆,一路拍着走。烟雾师在山顶放烟雾,以造成妖怪出没的效果。
上山时还算好,尽量少拍带马的镜头。拍戏时就让猪八戒拉着,不拍时,马的主人一路使劲拽着它,帮它使点劲。下山可惨啦!它的腿一个劲地抖,下山的山路狭窄拐弯处,它就拐不过来!我们的人拉着它的尾巴,它的主人拽着笼头,旁边还有人护着,怕它掉下去!
不管怎么样,这集总算凑合过去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买一匹白龙马!
《三打白骨精》拍完后,1983年的6、7、8三个月,我们在北京摄影棚内拍摄凌霄宝殿,蟠桃园,南天门等内景戏。9月份,我们到内蒙锡林浩特去拍孙悟空天河放马的戏。
使我高兴的是,这里有许多好马!里面有两匹白马,一匹最漂亮,高高大大,很有精神,一根杂毛也没有。但它的性子很烈,一般人都调教不了它。另外一匹白马是骑兵团团长的。它个子稍微小一点,样子一样漂亮,只稍稍有几根杂毛,可是脾气温顺多了。它驮着“唐僧”在马场过了好几天,我们的戏也拍完了,他们也处熟了。
临走前,我向马场的负责人问起可不可以把这匹马借给或者卖给我们?他们表示:按道理,军马是不能卖的,除非除了军籍!但如果我们为了拍摄需要,他们可以向领导汇报。我对他们说:马是一定要的,我会再和他们联系,请他们等我的消息。
回京以后,我向制片部门提出要买白马的事,没想到两个制片主任大为反对。他们提出增加一匹马会增加几十万开支——到处要用车皮,还要有专门养马的人工,会增加多少麻烦等许多理由。我则坚决要买下这匹白马。难道以前因为找不到白马而产生的麻烦还少吗?更别说白马总是变样,已经直接影响了艺术质量;再说根本不会有那么大的开销。争来争去,弄得面红耳赤,急头白脸,谁也说服不了谁!我就直接向领导打了必须买白马的报告。领导很快批准了我的申请。
我立刻和马场的同志联系,问问是否可以把那匹白马卖给我们,谁知他们已经把这匹马除了军籍,只等我们的消息了。只要给八百元钱就能给我们送来!没有几天,这“第四个徒弟”就到我们剧组来报到了!
这“第四个徒弟”没有辜负众望,它四岁就来到剧组,跟着我们转战南北,跋山涉水,一共相处了五年!
有两个人专门伺候它的生活,长途时坐火车,它和道具服装在一起,共用一个车皮,这两个养马师傅和它一起坐在那闷罐车里。因为是慢车,他们有时要在闷罐车里坐上十几天!短途时是用卡车运送。
养马的师傅非常尽力,不论白天夜晚,马的饲料都不会短缺。不多久,它就被养得皮毛光滑,更加漂亮精神,真有个白龙马的样儿!
白龙马的前身——龙宫三太子应该是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由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王伯昭扮演。他要在龙宫与龙女开打,还要在武夷山与悟空对打,必须会些武功。王伯昭不会武功。我问他,武打部分的戏是用替身还是愿意亲自上?他希望自己能学些武术,不愿意用替身。我有点怀疑:这不是一时片刻的功夫,只有几天的时间就得拍!他能学成啥样?也许还得备着替身。但王伯昭不怕苦。林志谦一招一式地教给他,他连摔带打地用心学。到了该拍他的戏时,他果然摸爬滚打的还真不错!我对志谦说:“这是两个人的功劳!教的学的都好!”
三太子变成了白马,王伯昭以后又在1985年1月军艺礼堂拍了《扫塔辨奇冤》里的龙宫夺宝、闹洞房等内景戏,之后就离开了剧组。后来那年的4月,我们在昆明的昙花寺拍摄白龙马救唐僧时需要三太子本人的形象,可是找不到他。他的单位没有人,那时也没有手机。怎么办?我想了个招儿:让白马来试试。让猪八戒逗弄白龙马,声音大一点,我们把录像机对着白马,录下它所有的动作和反应,然后配上画外音,试看效果如何?我们本来准备拍它一个晚上,看看能不能得到合适的镜头。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想,我们这匹可爱的白马,居然和马德华对着演成了这段戏,它点头,抬头,咬住猪八戒的衣服,看起来天衣无缝!
这匹白马非常通人性。每当想起它来,我就像想起一位朋友。它不是一匹马,而是一个人!它是那样勤恳忠实,从不偷懒,永不背叛。它不能说话,但却可以用它的目光表达感情。它在拍摄的生活中,曾经经历过几次险情。这几次险情都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
那是在苏州的一天,剧组出发前,白马每次都要上卡车。它必须踏上一块斜搭在卡车上的木板才能上车。这次,它不知是踏空了还是踩滑了,一下就摔倒了!身体卡在了房屋前面的水沟里,身上还驮着笨重的马鞍。它倒在那里,四蹄挣扎着努力想站起来,但马鞍卡在水沟里,使它站不起来,人们也拉不动它。大家忙乱着去拿东西来弄它起来时,它无助地倒在那里。我心疼地蹲在它面前,安慰它:“你疼吗?你怎么不小心些?别着急,我们就来拉你起来的!”
这时,我居然看到它的眼睛里流出了泪珠!真的,一大颗泪珠!天啊,它就像听懂了我的话,伤心得流泪了。当时,我也要几乎哭了。因为我感觉到它心里有那么多话却说不出来,这种无法表达的痛苦不是我们人类所能理解的!
好在大家立刻拿来了工具,七手八脚地把它扶着拉着弄了起来,然后拉着它在院子里走动走动,看它有没有受伤。活动了一会儿以后,它就行动自如了。我一直担心地看着,直到它小心翼翼地走过那个加宽了的木板,上了卡车。我望着它,不知道它那惊魂未定的心是不是安定了下来。
还有一次,是1987年的6月,我们在九寨沟拍摄《错堕盘丝洞》。我们拍完了瀑布下面的戏,准备拍摄师徒四人在瀑布上面行走的镜头。人们拉着它和师徒四人从另外一条路上往瀑布上面走。当时我和摄像师、场记等人在山下等待,只听见远处一阵嘈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切都是他们后来告诉我的:
就在上坡的时候,在非常湿滑的石头上,它又滑倒了,躺倒在乱石沟的缝里,山沟里淌着急流的水,冲击着它。大家都慌了手脚,急着想把它从水沟里拉出来,但是这次可不像上次,乱石沟比较深,水流又急,真怕把它呛着,但是水沟旁边的地方很狭窄,大家挤在那里,不管费多大的劲也拉不出来,两个养马的人也束手无策。围观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能帮上忙的。
这时,有一位游客过来了,他推开了我们的人:“让我来!赶快先把它身上的马鞍卸下来!”
我们的养马人赶紧卸下马鞍,这位游人叫大家让马休息一会儿,让大家听他的口令,一起使劲。几十秒钟后,他拉着马的缰绳,一声呼喝,一蹬缰绳,大家一同使劲,我们可怜的白龙马就势从水沟里站起来了!
那位游客,是一位藏族同胞,是一位专业的养马人!难怪他了解马的习性和需要,他和马的关系和比我们大家都要亲密,他和马默契到不用语言就能沟通。
白马站起来了。师徒四人和它又上了路,到我指定的瀑布上面拍完了师徒们行走的那个镜头。他们回来后,我听说了详细情况,感到自己太残忍了!在它经历了那样痛苦的事件后,还要它若无其事地继续拍摄!如果是人类,他起码会要求休息片刻,可是它是一匹马!它不能够诉说痛苦,不能提出要求!
第三次,是7月份,我们从九寨沟回来在灌县的二王庙拍摄蜈蚣精的戏。
进庙时,为了方便,我们从庙的后门进去,走向事先选定的景点。白马走在我们中间。二王庙是依山而建,从后门的许多台阶一路往下。台阶旁边是一溜排水的水沟,水沟旁是个水泥的斜坡,白马就驮着“行李”在斜坡上走。大家新到一个地方都挺兴奋,一路上嘻嘻哈哈地聊着天。
没想到,险情突然发生了!路旁有一棵歪脖子树,倾斜地伸向路中央。我们的白马本来完全可以过去,但是它的身上的行李包撞在树上,马就一下子腾空掉进了旁边的排水沟里,走在它旁边的徐霆雷被马撞了一个跟头,小徐身体轻便,就势窜到了旁边,落到了沟里。这排水沟很宽,长年是湿的,还长着青苔,很滑,地势又很陡,所以白马虽然是站在沟里,却站不住,一直往下滑。这水沟是直通的,没有边,水可以一直流到下面去。这次的危险是最大的!如果拉不住它,它就会掉到下面去!
这时大家都奋不顾身了:项汉一个箭步跃到水沟里,用自己的身体顶在马前面。但他的力量远远不够,他和马一起向下滑。徐霆雷则在马的旁边,拼命地抱住马腿。其他许多人都扑上来,有的揪住马尾巴,有的拖住马鞍,从各个角度想拉住我们的白马,但他们还是跟着白马一起下滑!眼看快到水沟边,就要马毁人亡!但是就在将要达到边缘的那一刻,因为水沟的坡度稍微缓了一些,加上大家的努力,这番生死拼搏终于停止在水沟的最边缘。
可怜的白马,可爱的小伙子们!虽然我记不住当时所有参加抢救的人,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至今让我感动不已!
匆匆五年过去,我们的戏拍完了。一切都有结束的时候,我也得和亲爱的白龙马告别了。
它在我没有能力顾及到它的时候离开了剧组,不知被人弄到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它和我们剧组所有的布景道具一起,被弄到无锡去了。还听说它被人当做一景,在无锡搞了个卖点,立了个“《西游记》的白龙马”的牌子,游客出××钱就可以和它一起照相,出××钱就可以骑着它照相,出多少钱就可以溜一圈……我听了这个消息真是太吃惊了:它居然被当做卖钱的工具了!它可是《西游记》的功臣哪!它辛辛苦苦五年多,风里雨里,爬山越岭,出生入死好几次,这不应该是它的下场。但是我自己都深陷于痛苦之中,无力自拔,哪有权力有能力去为它鸣不平呢?从它的遭遇,我深深感受到人类的冷酷。
多年以后,我记得是1995年,为了拍摄《司马迁》,我们到无锡基地去采景,我特地打听这匹亲爱的老马的下落。基地负责人说:“它还在!它如今享受退休干部待遇:住单间,吃小灶。”
于是我立刻去找它,看看它到底如何“享受退休干部待遇”的。
我们走到基地边上半山坡一条靠墙的小路,发现路边贴墙的地方有一间像洞穴一样的小“屋”,其实只是一个山坡上挖出来的洞窟,很阴暗,很狭小。靠近门口还算有点光亮,那里有一匹孤独的瘦马,独自无精打采地嚼着马槽里的稻草。这么远就能闻到屋里满是马粪味。它很脏,几乎看不出它原来的白色,这就是我们的白龙马?我不禁沿着小路走到它跟前,从近处打量它。它回过头来,望着我。我震惊地认出来了,它就是我们当年一同共过患难的白龙马,但是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精气神。
我轻声地问它:“你还认得我吗?老朋友?”
它一动不动地望着我,眼里没有表情。
我又问它:“这些年,你过得好吗?你怎么这样瘦了?他们给你吃得饱吗?”
它仍然在专注地听着,一动也不动。我不知道它脑子里有没有想起当年的日月?
“我们来看你了,你还记得《西游记》吗?记得吗?你想我们吗?”
这时,可能别人以为我神经病了,一个劲地催我:“它听不懂!快走吧!”
我们离开了,我一直回头望着它,它也一直望着我,我觉得它认出我来了。我站住了,因为再走一步,就会走出它的视线。这时我大为惊异:它叹了一口气,有些怅然地回过头去了。
我吃惊地对王崇秋说:“它叹气了!它认出我们了!”
他不信。我却相信,它那一声叹息里包含了多少悲苦!我从心底感受到了:这就是它无言的回应。
我向基地的领导提出我的希望:“把我们的白马照顾得好些,它是有功的。《西游记》有它的血汗!”他们答应了,但是又附加了一句:“现在够好的啦,马活不了多久,也该差不多了!”这句话使我寒心,有这样的想法,能好好地照应它吗?
1996年,我在无锡唐宫拍摄《西施》,又去找寻它的踪迹。但这次比较难,已经没有人去关心什么“白龙马”了,好多人不知道它在那里。后来才打听到,它和马群一起,养在马厩里。于是我们几个人又到马厩去找它。但是到处都找不到,那里都是棕色红色的高头大马,就是没有白色的马。问到马厩管理员,才知道它就在马群里。
我们终于发现了它!可是令我大吃一惊:它矮小,瘦弱得不成样子!它就在马群里,却被遮挡得看不见。这就是我们的白龙马?真令人不敢相信。它怎么变成这样了?现在是马群开饭的时候,在这些高头大马中间,可怜的它根本挤不到马槽前。那些年轻力壮的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把它挤到一边。它只能畏缩地躲开,免得被它们踩到。
我们在马圈外观察了好一会儿。我心痛地看到,它竟然连一口吃食也无法得到。它又老又无力,不被踩死也会饿死,真是一幅悲惨的情景!我预感到,像这样下去,它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也许这就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它。我让管理员把它牵出来,让它和我们一起照个相,留下一个影像,就算个最后的纪念吧!
在这个心酸的时刻,我对它说:“你还认得我吗?我们都老啦!”但是我感受不到我的白龙马的任何反应,它已经衰老得对外界的一切都木然而无动于衷。它只是低垂着头,仿佛连抬起头看我们一眼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不是和人的风烛残年一样吗?如果没有人来关心它、爱护它,它的生命也许瞬间就会消亡了。我心痛难忍,当时若不是有别人在身旁,我真会为它痛哭一场!
我气愤地问管理员:“你们知不知道它就是《西游记》里的白龙马?能不能给它改善一下现在的生活条件?难道没有注意到别的年轻的马欺负它,它根本吃不到东西吗?为什么不把它分开,单独给点吃的呢?”
他满口答应,把它牵到另外一间屋里去了。他大概心里奇怪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这么关心它吧。
我们离开了。不知道我们走后,那可怜的“白龙马”是否能够吃到一口食物?
第二年,我听说我的“白龙马”死了,它就埋葬在基地里,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我无语!
我想起当年在内蒙古草原拍摄马群时,那可爱的白马是多么英姿挺拔,它和朋友们一起在草原上尽情驰骋,抖着长长的鬃毛,迎风长嘶。那时的它多么年轻,多么快乐。是我把它从朋友那里夺了过来,使它过上剧组的生活,让它和我们一起,辛辛苦苦,走南闯北,当上了“白龙马”。但这对它有什么用呢?这并不是它自己的选择。它再也没有了朋友,是那样孤独。等到它被人们利用完了以后,就被冷酷地抛弃。现在,它因为衰老而被排挤,被疏忽,被看成了累赘,于是默默地死去。它的心情又有谁去关心,谁能理解呢?其实,人和马一样!到了没用的时候,谁还会关心你的生死呢?人尚且如此,何谈一匹羸弱不堪、不能讲话的老马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