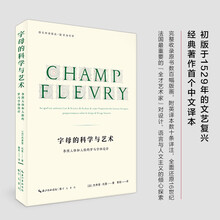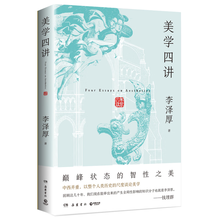第1章 建筑史的“镜像”<br><br><br>建筑史的“镜像”<br><br>古典建筑的历史似乎是在18世纪中才突然被发现的。倒不是说在此之前没有建筑史,而是说,只有当人们有意识去梳理历史时,历史才会浮现。自布罗代尔出版第一部建筑史之后,欧洲迈进复古主义时代,建筑师纷纷从希腊、罗马和哥特式建筑中寻找风格的依据。贯穿于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就包含了各种对于历史的想象和解释。<br><br> 全然的复古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人们从哥特式教堂的尖顶竞争中恢复了理智之后,塞利奥就重新为西方建筑寻找到了真正的源头——希腊和罗马建筑。然后是巴拉蒂奥开创了建筑考古学的传统。尽管萨默森早就指出:巴拉蒂奥的考古学,经常是想象多于现实。这种现象对我们却是一种难得的启示。从15世纪以来,西方建筑的每一个阶段都创造出某种古典建筑的“镜像”。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每一面镜子里映射的希腊、罗马建筑其实都渗透着建筑师的个人意志。然而在历史现实中,个人消隐在古典希腊和罗马建筑的光环之中,建筑师自然也乐得如此,似乎不如此就不能获得建筑的合法性。所以,一直到19世纪中叶,古典主义建筑完全如同萨默森在总结古典柱式的传统时所说的:既恒定一义,又能够适时有所表现。<br><br> 看来,对历史的认识程度并不会影响建筑生产的实质,只要每一个时期的建筑师自信地以为他们复原了古典建筑的正宗样式,每一代的建筑都被创造性地建造出来,同时又成为整部历史的一部分。关键在于,无论与古典建筑的传承关系如何,建筑都是适应和服务于现实的产品。建筑物既是由石块、雕刻和砖瓦等材料构成的物质实体,也是精神的载体。在精神和象征的层面上,建筑联系着社会统治中的权力格局。舒尔茨在分析巴洛克建筑时说:巴洛克建筑中,主要的纪念性建筑是教堂和宫殿,它们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两种基本权力。如果没有耶稣会为了增加宗教权力而发动的建筑竞争,巴洛克建筑中繁琐得无以复加的装饰风格可能也无从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巴洛克式的山花与涡卷装饰与宗教权力有着明与暗的关系。<br><br> 在建筑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不是样式的创造,而是样式与现实权力的“对位游戏”。在19世纪初,当巴伐利亚王储路德维希为了纪念打败拿破仑而修建英灵纪念堂时,建筑师克伦策毫不犹豫地为位于雷根斯堡的纪念堂选择了帕特农神殿的样式。象征的逻辑如此:希腊人打败波斯人的经历与德国人击败拿破仑相类似,于是帕特农神殿的建筑样式也就顺势被挪用于象征民族英雄。在这里,帕特农神殿就是某种历史的“镜像”。两千年之后,它还能适时地从克伦策的手中显形出来,照射出新兴的普鲁士民族—国家的国家精神。另一个例子是托马斯·杰弗逊,这位美国式民主制的开创者尤其热爱希腊神庙建筑。结果,他把弗吉尼亚州议会大厦搞成了一个梅宋卡瑞神庙的复制品。他认为,举世公认的典范之作好过任何建筑师的个人想象。显然,杰弗逊的选择告诉我们,复古的任务分为两个:一个是寻找古代的经典建筑样式,另一个是为古代经典找到符合社会现实的用途。当然,建筑师手中的“镜子”必须照射出政治家能够接受的内容。政治间接地操控建筑似乎是个普遍规律,这与社会制度的优劣有何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关于这个现象,我们从20世纪的北京城和天安门广场的改建计划中完全能发现相同的道理。只不过五十多年前,梁思成先生的“历史之镜”没有能囊括新时代的内容,中国式的古典主义“镜像”最终还是遭到肢解的命运。<br><br> 毕竟建筑的历史还从未中断过,这样或那样的特殊性造成了各种建筑和建筑史的“镜像”。没有现代主义,古典主义的轮廓是不完整的。只有当整个古典建筑史都成为现代主义的“镜像”之时,“古典”才终于找到了永久的栖身之地——与现实交相辉映。如此说来,历史与现实一直是在“互为镜像”。<br><br> 建筑是历史的,还是现实中的?这个问题还是由大家来回答吧。<br><br>中国风和民族化<br><br> 18世纪中期,东方的装饰风格渗透进了法国宫廷。从皇帝到贵族,一度以拥有精美的中国瓷器、丝绸等奢侈品为荣。在英国,“如画风格”正在改变着丘陵起伏的田野和庄园的景致。那时,东方的中国也成为某种引发想象力的因素。1757年,威廉·钱伯斯出版了一本论述中国建筑的书,在建筑领域里造成了不小的反响。的确,中国园林的自由、不对称的造景手法与几何化的西方园林大异其趣。但是,异国情调充其量只是些迷人又短暂的时尚,关于这一点,柯林斯说过:过去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建筑师的理想很少是来自东方的。事实上,东方风格的字眼常常与“古怪”、“异常”等词汇一样带有某些贬义的成分。<br><br>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礼赞的那个中国到了19世纪就几乎烟消云散了。中国仍然在向西方世界输出大宗的瓷器、茶叶和丝绸也无济于事。作为西方人建构的最主要的一个异域想象,中国进一步滑落为停滞、愚昧的象征。在轮到中国和日本来想象一个先进的西方世界的时代里,中国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日本甩到后面。但在建筑领域,中日两国的处境很类似,过去由西方人想象的东方建筑风格——所谓的“中国风”与“和风”,都同样遭遇到一个最强大的挑战者——“洋风”建筑。<br><br> 只有在中国和日本面前,西方风格才被称为“洋风”。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洋风”无异于现代化。19世纪末日本式的现代化是在国家政体上完全模拟西方建立一套议会式政府。当要为新式的政府选择建筑形式时,却面临着两种选择。德国建筑师鲍库曼曾为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做过两套方案:其一为彻底的西洋式建筑,其二戴着传统日本建筑的屋顶。鲍库曼的“和风”方案似乎是折中主义建筑的一个源头。不过,“和风”方案最后遭到了否决,选择新古典风格的国会大厦与日本的全盘西化策略完全吻合。自此,“洋风”建筑便彻底取代了日本传统。日本的现代化(工业化)过程证明,现代化程度与文化困扰形成反比。自丹下健三之后,日本建筑师已不再属于日本,而是晋身为发达国家建筑俱乐部的主要成员。<br><br> 建筑风格的困扰更多发生在处于第三世界却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家。最典型的当属近代中国。困扰的实质无非就是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双重变奏。20世纪的中国建筑史表明了这一点,因为有了强大的民族化目标,中国建筑也从未实现真正的国际化。民族化的表层意思是拒绝被同化,深层意思是要编织出隔离外部世界的藩篱。中国建筑师也就被塑造成双重身份,他们既是职业建筑师,还得是个民族建筑师。实际上,民族化一直是个超越建筑本义的政治目标,在政体建筑上寻找各种复兴传统建筑风格的方式在民国时期就达到了顶峰。之后,民族化的建筑逐渐滑向图案装饰。到了20世纪90年代,民族化居然被简化为“古都风貌”,解决的方法是在一系列高楼大厦上拼接中国式亭子。这几乎成了新恶俗的源泉。<br><br> 话又得说回来,那些最希望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新锐建筑师也同样无法摆脱民族化的困扰。既然中国身份不可推卸,那么,巧妙地打出“中国牌”反而成为中国年轻建筑师的制胜法宝。“非常建筑”的张永和在南宁的城市设计中提出“竹化城市”的概念,就明显包含有“中国风”的意味。来自西方的先锋建筑师巧用中国符号的手法更是令人眼花缭乱。赫佐格和德梅龙在北京国家博物馆改建的提案中创造了一幅水墨画的屋顶,我以为这是“中国风”被运用到登峰造极的实例。我尤其注意到,在巴塞罗那的城市更新计划中,赫佐格和德默龙也应邀设计其中一座会议中心,那是个平面呈三角形的庞大无比而风格前卫的建筑,位于更新区域的中心。但是,这幢建筑没有包含任何西班牙民族化的目标,巴塞罗那的总建筑师说:希望巴塞罗那成为欧洲最大的公共空间实验室。这个城市的市长接着表示:巴塞罗那要继续成为欧洲领先的城市。简而言之,这是欧洲的游戏规则,当然也就是国际式的。<br><br> 当我们被围在“中国风”的篱笆里眺望外部世界时,就只能告诉自己: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个道理是否能反过来推论呢?<br><br>铁路、建筑与文化冲突<br><br>庚子赔款几乎断送了憎恨火车的慈禧太后的末日江山,却造就了容闳带到美国留学的120名幼童,在他们中就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一个是拒绝铁路运输的深宫皇后,一个是创造性地解决了外国人也没解决的工程难题的天才工程师。就这两者来看,中国迟迟不肯迈入铁路时代的主要困难肯定不全是技术因素,而是深层次的文化冲突。由铁路的命运想到建筑的风格,我们应该更好理解,为什么同样留美的梁思成先生在学成归国后,竟致力于挖掘和整理中国古代建筑遗产。于是我们也不得不说,虽然梁先生之于中国古典建筑研究的热情与贡献无人可及,但他的研究理念受益于宾州大学“鲍扎学派”的教育。梁思成可能是黄仁宇提出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典型例子。中国本来就有悠久的营造史和丰富的建筑遗存,而把“营造法式”中的大木作经验整理成一套民族建筑艺术体系,这种观念却真的源自西方。<br><br> 与铁路相比,建筑当然更是属于文化的。所以,建筑师必然要比铁路工程师面对更多的文化困扰。铁路之于慈禧可能是悖逆祖宗的“奇技淫巧”,可对于詹天佑就不过是技术挑战罢了。火车最终还是驰骋在旧中国的大地上,也没有谁会提出“铁路民族化”的说法,这是因为铁路毕竟与风格无关。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末的欧洲,无人去阻挡铁路的扩张,但是有人居然不承认火车站也是一种“建筑”。理论家拉斯金就是一个代表。他甚至于在《建筑学的七盏明灯》里说:建筑有别于黄蜂窝、老鼠洞,或者火车站。拉斯金瞧不起火车站的态度与慈禧太后根本不同,他不是拒绝铁路,而是要把火车站从建筑艺术的行列中排斥出去,归根到底还是与风格判断的惯习有关。拉斯金固执地要保持古典建筑艺术的尊严,这种态度不过预示了古典建筑的没落和现代建筑的来临。在中国,建筑风格的问题往往要复杂得多。20世纪早期,建筑风格常常是两种文化冲突挤压的结果。因为有了外来的西方建筑样式,这个问题通常只能有三种答案:西方“洋风”式,中西结合的中国式,中西结合的西方式。后两者是对于前者的回应,暗含的目标都一样——建筑的民族化。<br><br> 完全由西方人建造的西方式建筑其实早在四百多年前就出现在珠江口的澳门,然后现身于广州的商馆区,跟着蔓延至沿海口岸的租界,最后在上海的外滩形成规模。外滩的商业建筑群在风格上几乎都是舶来品,无论是汇丰银行还是沙逊大厦的设计师,都谈不上受到文化冲突的困扰。因为从本质上来说,文化冲突的焦虑只会发生在弱势的一方。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西洋建筑风格以压倒性的优势进入中国时,主动去恢复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又是西方人。起源点是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之后形成了民国时代最典型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从表面上看,西方人热衷于中西结合式的建筑样式是审美的偏好所致,但实际上还是文化策略的成分更大些。为什么复兴传统的建筑风格几近变成南京政府的建筑“国策”?这说明在冲突的现实中,建筑风格确实是关乎民族尊严的大事。<br><br> 其实,中西结合的建筑还是有个中国式和西方式的比重问题。墨菲设计的协和医学院虽被指责为拼凑,但我还是宁愿把它归类为“中西结合的中国式”,以区别于后来以杨廷宝为代表的“中西结合的西方式”——中国式成为西方式的装饰附件。风格的命运的确不好预测,无论怎么说,还是杨廷宝先生的人脉最旺。新中国成立后,从民族文化宫到毛主席纪念堂,同样的风格传承都能被发现。<br><br> 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建筑民族化可能已不时髦了。今天,西方建筑师和海归派共同驾驶着中国当代建筑的火车头。与近百年前相比,建筑领域的文化冲突可能更多地转化为利益份额的冲突。而解决之道则有了挺大的进步——把民族化置换成“文脉”,我们似乎正在创造又一个中西结合的新高潮。<br><br>兽头与柱式<br><br>两百年前,中华帝国的建筑映入了来访的英国人的眼帘,他们既惊讶又感到奇怪,因为据他们看来,“(中国的)寺庙和宫殿或者漂亮的王府没有区别,根据风水,所有的建筑都是坐北朝南,屋顶都呈角形,上面有一些守护神的小塑像或者令人生畏的兽头”。<br><br> 西方式的认知虽然很粗陋,不过也多少表明了这一点:与西方建筑相对照,中国建筑有着大一统的风格。归根结底,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建筑的样式的意义也必须在“文化显影液”中才能显现出来。就拿屋顶来说吧,与哥特式教堂或巴洛克建筑相比,中国木构建筑的屋顶可能都差不多,而在中国营造体系的社会意义上,建筑的形制与等级却很分明。同样都“呈角形”的屋顶分为庑殿顶、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屋顶的等级自不必说,即使那些“令人生畏的兽头”(其实是屋顶上的琉璃瓦脊饰,称为吻兽和小跑),在样式、排列和数量上也有着严格的规制。把屋顶样式与瓦件装饰合在一起,中国建筑的屋顶与大清官员的补服和官帽上的顶子一样简明易懂。建筑有如另一套等级语言,成为确保整个社会制度运行的符号工具。此种意义,当然是来自彼文化中的人难以读懂的。<br><br> 在西方建筑中,与中国式屋顶形成对照的建筑元素是柱式。从维特鲁威开创的柱式原型到塞利奥确定出的5种标准的柱式,在两千多年的跨度上,5种柱式成为“长期的、象征性的、几乎统治一切的”建筑要素。木构的屋顶和石构的柱式看上去差异极大,不过有一个特点却是东西方建筑所共有的,正如萨默森提出的疑问:为什么是5种柱式而不是4种,或16种、326种?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正式建筑”的屋顶分成了上述4种之后,也没有无止境地分化下去(园林或杂式建筑除外)。这个问题,可能还是要回到建筑物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上来解答。社会的共性是形成统治的结构,文化的共性则是不断地突破技术或风格的条件。即便中国的鲁班门徒和西方的主工匠具有不断创新的“本能”, 只要在特定制度的约束下,屋顶与柱式都会倾向于达到变与不变的均衡态。如果社会统治者从屋顶和柱式的变异中得到的收益太小,4种屋顶或5种柱式可能就成为某种临界点。显然,样式的无穷演变不仅导致等级识别的混乱,还是一种“文化浪费”。联想到中国的九品文官制,为何是九品,而不是十五品?这也与社会统治的均衡态有关。在表达等级的方法上,大清朝的官服是最节约成本的样板,清一色的蓝色大袍上裰以不同的“补子”来分辨等级,这个办法要比18世纪法国宫廷五花八门的假发、礼服和花边服饰节约成本。反过来说,法王路易和他的贵族们要比中国官员更热衷于个人炫耀,以炫耀为原则,夸张的法式装束也有着外人难以读懂的等级含义。<br><br> 问题出现在相异文化的碰撞之间。1793年,绕道北上的英国使团在浙江定海上岸,身穿“窄得包身的欧洲服装、涂有发蜡”的“红毛人”自居为世界主人,却遭到中国人的围观和哄笑。可是两百年后,西方建筑中的5种柱式却如飞蝗一般席卷中国大地。当柱式掉进了中国式的“文化显影液”里,全被笼统地称为“罗马柱”。15世纪的塞利奥要是看到中国人如此大规模运用他的柱式,会作何感想?当代中国“建筑师”对于柱式的使用可谓无所顾忌又登峰造极。想想也是,柱式本不是原产地文化,也与我们的制度无关。柱式不过是谁都能用的时髦符号。于是从乡村中的新住宅到高新开发区的门楼,从豪华酒店到政府建的市民广场,从珠三角的东莞到浙江的温州,“红毛人”的柱式成了泛滥成灾的炫耀道具。<br><br> 当然,节约与炫耀的双重原则到了今天仍然有效,过分泛滥既不节约,也会使炫耀丧失独特性。柱式在中国的命运表明:失去了文化与制度的约束,流行的“罗马柱”不仅会比“令人生畏的兽头”还要可怕,而且只能滑向庸俗和遭人哄笑的谷底。其实这一天已经到来了。 <br><br><br>县衙门的空间政治<br><br> 依照古典中国“皇权不下县”的惯例,县衙的所在成了区分乡村与城镇的主要标志。衙门是中华帝国的权力金字塔中最基层的政治机构,对于散居在田野乡村的百姓来说,县衙门好像是远在天边的皇权延伸到近旁的行政终端。我们把清以前的皇权政治想象成一种出售行政产品的营销系统,衙门如同一个设在县城里的供销百货站。今天的家电产品销售或新华书店也是以县城为单位设置销售终端的,这一点实在与古代中国的政治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处。<br><br> 接下来我们看看什么是衙门的形象。一般来说,衙门都由一组院落组成,因此它是个有相应规模和建制的建筑群,它又被划分为公与私、外与内两大部分。首先让我们看看对外为公的部分。衙门是一个处理公共事务的机关。县老爷就是一县之民的“父母”。皇帝赋予衙门的任务主要有两个:一是征缴税赋和处理诉讼,二是兴教劝学。这种目标导致了衙门的外院结构。相对讲究威严的大门之内,受皇帝委派的国家任务——监狱和粮仓——安排在外院的左右两侧。这里也是书办和衙役的活动空间,他们在县官的督导下,具体负责处理城乡的公共事务。因此,从角色和身份来分析,这个空间格局也是滋生出不同利益诉求的场所:一是要落实皇权事务,这是县官的职责所在;二是由书办和衙役代理地方士绅势力的利益。而两种利益的份额并不确实。换句话说,皇帝的恩典到了县老爷身上就到了头。薪水菲薄的管事小吏必须从当地的复杂利益冲突中谋求福利。这样的管理架构实在是很容易演化出某种“恶棍政治”的局面,衙役与乡间恶棍们为了自身利益常常会尽可能地挤占皇帝的利益,别说是皇帝,就是连县官本人恐怕也奈何不了他们巧取豪夺的本领,盖因县官坐在“治堂”办公,而治堂的后面还有一个县老爷自己的内院在。<br><br> 分为两重的内院里,人马也分为两拨:一拨是县官的私人幕僚(协办公事)和长随(主要是门卫),处在第一重内院;另一拨是县官的家眷奴婢,处在第二重内院。幕僚通常是精通行政事务的“职业经理人”,其作用不言自明,而长随的身份就要隐秘得多了。正如密迪乐所指出的:他们是所有专门贿赂的谈判者,也是把官吏的其他非法所得引入他的私囊的渠道。看来,县官虽然不得不履行皇帝托付的责任,清以后的“考成”制度也对县官的绩效和升迁构成压力。但是县官在集各种利益和职责于一身、行政经费又永远短缺的前提下,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来谋求平衡,而利益的天平又总是会难以遏制地滑向中饱私囊的一极。这样,长随/门卫的作用可就太大了。说到底,衙门的一个“门”字便道出一切,俗话说的“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骂的怕不是县官,很可能就是那些看门的家犬。正如约翰·R·瓦特所说:门卫能约束众人,管制衙门人员的活动……对正式和非正式人员的相互影响与公、私业务的相互渗透,能发挥相当大的控制作用。<br><br> 至此,衙门的空间政治格局已现出端倪。县老爷坐在内外院中间的治堂,分别处理皇帝和自己的事务,外院的衙役和书办纠合地方势力与县官的行政CEO(师爷)进行利益博弈,而长随/门卫却管理着整个衙门的进出权,像“看门狗和暗探”一样划分公与私的利益份额。虽然院墙隔离了内外院的联系,这是为了断绝正式(衙役)和非正式(幕僚)下属官员之间谋划私利的机会,但是从衙门院落的整体格局来看,空间上的二元结构仍然受控于一元化的长随/门卫。在他们的钳制下,皇帝和官吏会有怎样的社会声誉就可想而知了。不过,除却民众疾苦和社会声誉的参数,衙门的利益产出还是颇有效率的。据张仲礼不完全估计,清代知县的年入为白银3万两。可以想象,在这个表面森严、其实却明争暗斗的院落里,能在空间中谋到一个位置的人还能少得了拼抢来的份额吗?<br><br><br>红色经典与国家想象<br><br> 自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后,紫禁城就一直是天下的中心。满族人的入主虽然颠覆了朱明王朝,却把旧朝的制度和文化一揽子接收下来,包括巍峨的皇城。确实,与努尔哈赤的盛京(沈阳)比起来,只有北京城的中轴线建筑群才真正具有普天之下、唯此为大的意象。由明入清,大明门改成了大清门,承天门改成了天安门,改朝换代简化为统治权的命名法。盖因朝代可以更迭,但天下的秩序仍然运行不悖。<br><br> 到了辛亥革命后,国家取代了天下。既然天下的秩序大变,紫禁城就不再是君权天授的空间象征,皇城易名为故宫,大清门改为中华门。整个北京城中轴线上的建筑群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中退身出来,成为最大规模的民族建筑标本。国民政府自放弃北平、定都南京伊始,就一直在寻求新的民族—国家形象。吕彦直的中山陵代表了南京政府对于折中主义风格的偏好。民国式建筑的国家形象由传统的大屋顶和西洋式的建筑格局混合而成。不过这种造型正好与民族—国家的观念相吻合:大屋顶象征着民族,西式建筑格局则象征着现代国家政体的性质。但是,民国的折中主义建筑固然典雅和精美,却很难体现恢弘的气象。“民国式”建筑延续到台湾后就到了尽头。1949年之后,新中国再次重新寻找符合国家政体性质的空间象征就显得势在必行。<br><br> 这一次,焦点又再次引向了北京城。天安门从中轴线建筑群中脱颖而出,它不再是旧皇宫的外城门,而是被塑造成历史的屏幕。它的后面是有名无实的古典型权力中枢;在它前面,历史建筑必然要遭到清除,这样才能打造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广场空间。天安门广场重构了中轴线的空间秩序前,也为寻找新的民族—国家形象奠定了基础。在天安门前,“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古训已不大管用。人民英雄纪念碑就像嵌入到中轴线上的时代坐标,以它为核心,西边是人民大会堂,东边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整个组合造出了符合新中国之国家意志的空间意象。<br><br> 这片空间注定是不同凡响的,但北京城的历史给国家形象的定位带来了困难。重构北京城的中轴线,等于让历史成为新国家权力的基底。作为政体象征的人民大会堂尚好理解,而历史博物馆与革命博物馆的建筑定位却另有含义。选择在最具有历史感的中轴线上建造一个历史容器和革命祭坛,而不是像梁思成先生所倡议的那样彻底保护历史,其实最大的目标只有一个——为了重新诠释历史。这一点也体现在命名上,将中国历史与革命历史放在一起,实际上恰恰是为了区分古典中国和新中国两种历史的性质。由此而得到的建筑形象出奇地大,长长的柱廊让人们想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建筑风格。它真正是个社会主义建筑的典型,拥有意识形态所偏好的宏大体量,里面的展品收藏却与它的规格形式不相衬。<br><br> 当历史之书翻到了200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要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意味着,古典中国史与近代革命史之间的界线已被国家的概念所涵盖。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国家的形象呢?<br><br>2004年,北京举办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国际招标”就是一场新国家形象的预演赛。与五十年前的拆旧建新正好相反,新的国家博物馆以历史主义为原则——任务书要求保留旧的历史与革命博物馆的四个立面。库哈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经典说在此得到了回应。这就是说,新的国家形象必须从红色经典的胚胎里产生出来。虽然不少世界一流的建筑师努力给出了别具一格的答案,但是,最有创意的,如H&D的方案却被放弃。我以为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无论如何,保持红色经典的原则使得张开济先生(原博物馆的设计者)要比梁思成先生幸运得多,在梁先生保护北京旧城的计划落空多年之后,国家的想象已经和整个天安门广场建筑群融为一体。此时,我们确实很难分清楚:旧北京的中轴线与新中国的政体式建筑群,哪个更具有中国精神?哪一个才更能体现国家的想象?<br>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