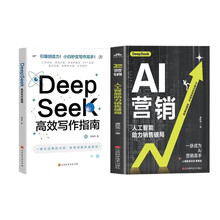在世界“五大文明摇篮”中,只有古希腊文明诞生于地处欧亚非交通枢纽的爱琴海沿岸,其他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四大文明皆起源于内陆的大河流域。本文以文明诞生地的不同特征为切入点对古希腊文明和华夏文明予以追溯,将二者区分为三个宏观的比较维度:“海洋文明”与“农业文明”、“复合文明”与“独立文明”、“城邦文化翟与”宗法文化“。这三个维度的相互综合作用,是东西方两大文明在早期构成”文明基因“的关键所在。在这三个比较的维度中,决定古希腊和古中国在文明早期形成不同生活样式和道德谱系的核心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二者在与各自的环境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精神气质“如何;其二,私有制发展的程度是否彻底以及血缘关系的亲疏强弱如何。
就”精神气质“而言,古希腊民族和华夏民族在与各自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至少演化出下列不同的生活样式和道德风尚:就古希腊而言,海洋本身的神秘与航海生活的险难,刺激着他们探索的欲望和征服的勇气;跨海的国际贸易活动,需要双方协商乃至公平交易的契约精神;大量的海外移民与民族融合,易于养成多元文化并存与开放的心态;地处欧亚非交通枢纽并且深受其他更为古老文明影响的史实,导致古希腊人长于借鉴和捷径式的发展;”小国寡民“式的城邦自治,致使各城邦形成对地方价值的珍视,等等。反观同时期的华夏文明,内陆农耕生活的确定性与安稳,易于形成稳妥与中庸的心态;自足自给的农业生涯,需要辛勤简朴与守成的品质;世世代代在固定的土地上过活,易于形成安土重迁和祖先崇拜的伦理德性;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独立发展模式,易于形成封闭自满的意识;大规模的国家与社会组织,容易形成大一统的权力和等级意识,等等。总之,二者在文明的萌芽期在与各自环境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精神气质“,无疑会对日后的发展路径和道德谱系建构产生规定性的定势发展。
就私有制发展的程度而言,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古希腊的私有制较之古中国发展更为彻底。其根本原因在于:古希腊在借鉴其他文明成果之后的捷径式发展、铁器的广泛使用、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和移民,等等。这些因素促使古希腊的生产力得以长足发展,剩余产品大量积累,私有制演进程度较为彻底。马克思曾经指出:“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古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①在早期私有制发展的程度上,古希腊民族属于“正常的儿童”。然而,古希腊的私有制宛若一把“双刃剑”,它在促使个体权利意识觉醒的同时,也割裂了氏族内部的血缘亲情,为城邦公民及其德性养成奠定了基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不过是为公民提供至善生活的手段而已。尽管在古希腊的城邦制国家中,妇女、奴隶和外邦人不在“参政的公民”之列,但是公民的资格也并非高贵血统的世袭特权。在雅典,统合个体公民日常德行的是经过“公民大会”合意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之上的灵魂则是与个体公民等距离的“多元神”信仰。
与古希腊人作为“正常的儿童”相比,华夏民族在私有制发展方面属于“早熟的儿童”。换言之,华夏民族在私有制尚处于远未成熟的时期即迈入了奴隶制社会。这意味着,氏族成员向奴隶和奴隶主分化的历史过程演进得不够彻底。由于剩余产品的交换和社会分工尚未得到普及,土地亦没有实现完全的私有化,氏族内部的血缘和宗族关系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得以顽强地延续。经过周朝“分封制”之后,更是强化了这种具有强烈血缘性和地缘性的宗法体制。实际上,分封制和宗法制互为表里,在家中或族内即是宗法制,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分封制。其根本特征大致有三点:一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为核心;二是族权与政权相结合,家国一体;三是宗法制、分封制、礼乐制互为一体。在这种“三位一体”的制度中,人的道德“品格”是由先天的血缘“位格”决定的。抑或说,在宗法制中血缘关系嫡庶亲疏如何的“位格”,是决定一个人是否有分封资格以及封邑大小的关键,而礼乐制则是根据宗法制中的嫡庶亲疏和分封制中的上下尊卑,按等级、有秩序地实施日常人伦和祭祖等道德活动的风俗和规则。
总之,在文明的萌芽期,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先祖们在与各自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精神气质”如何、私有制的演进程度以及氏族血缘纽带的强弱,是导致古希腊民族和华夏民族在相同的人类学前提下走向不同发展路径并形成不同道德谱系的根本原因。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