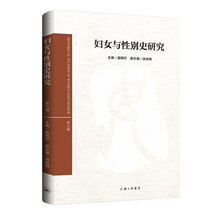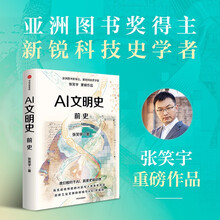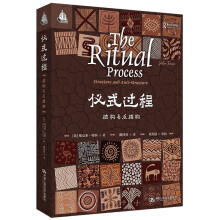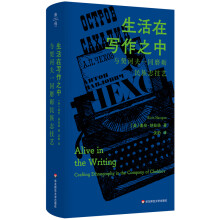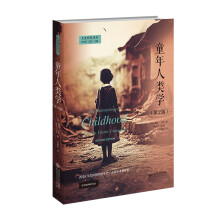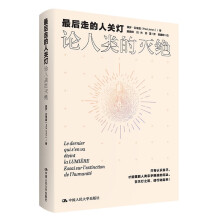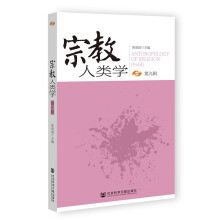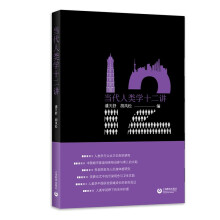(二)内部东方主义的幽灵
游客在旅游中都抱有猎奇心态,这种心态与好奇有所不同,后者多少带有某种探究的心理。对此,前者未必有。如何来满足游客的猎奇心态便成为旅游策划者和从业者的重要任务。在许多国家,国内的文化多样性和历史通常都成为旅游开发的资源。通过展示不同的文化来招徕游客是最常见的方式。但是,如何展现文化,尤其是展现非主流的文化或者展示非主体民族的文化?这是经常受到挑战的问题。在我国,我们看到,许多民族地区都充分利用本地区丰富的族群多样性资源来进行旅游开发。然而,在展示民族文化的方式上,援用的却是一些看起来在政治上不是那么正确的方式。换言之,在许多旅游景点里,少数民族之“异”往往是重点展示的对象。而且对所谓“异”的解释往往又有本质化之嫌,似乎他们因“异”而与主流社会或者主流文化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很明显,旅游目的地的许多景点在与旅游凝视的对接上,都有这样一种本质主义取向。换言之,景点的策划者都试图迎合游客的猎奇心。因此,原先可能可以发挥博物馆社会功能或教育功用的景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此背道而驰。它们所展示给游客的并非当地人今天的社会生活,而是不恰当地对当地传统进行的夸张。同时,由于长期以来所接受的教育和主流媒体的宣传,许多景点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描写与介绍完全与国家对民族分类的解读如出一辙。①比如民族村的解说员会介绍说某民族处于某阶段,信仰“原始宗教”,“文化落后”等等。这种似是而非的社会文化发展阶段的进步与落后甚至在一些策划和设计中成为某种元素,而这些元素一定与自然的风光山水相搭配。为此,设计者可以将与当地无关的族群或者民族置放在山水之中来娱乐游客。譬如,广西阳朔有一处利用当地喀斯特地貌的山形岩洞与水流构建起来的景点,名为“世外桃源”。游客们泛舟水面,穿行岩洞。在水路的两边山坡和崖面台地上,不时出现载歌载舞的佤族男女青年。佤族是生活在云南的山地民族,为什么要把他们安排到广西来?同在一条船上的导游姑娘的解释是,“因为他们最原始,也就最快乐”,于是与美丽的山水最为协调。这真是个奇怪的逻辑!按照这位导游的话,岂不越“原始落后”也就意味着越快乐,越幸福?这种逻辑的背后其实就是越“原始落后”,头脑也就越简单;头脑越简单也就越无忧无虑。如果卢梭“高尚的野蛮人”之说尚可以考虑为对“文明”的失望,那么“原始落后”与“快乐”成正比,则表现了“现代文明人”的无知与妄自尊大。其实,我们在众多民族旅游目的地景点所看到的是活生生的“他者”建构;而且还可能是一种自我的“他者化”——如果我们考虑到许多当地人也参与了这样的建构的话。
上述所提及的情形在中国许多民族旅游场合都可以听到,这绝非偶然。除了今天可以见到的各种涉及少数民族的古代文献都充斥着荒诞不经和歧视性的记载之外,当代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分类和与此分类直接相关的有关知识,也将少数民族嵌顿在一种“落后一进步”或者“野蛮一文明”的线性演化的梯度解释模式上。这种貌似理性分析的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解读,无疑给一般主流民众甚至少数民族民众自身建立起一种有关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另类的刻板印象。因为它貌似理性,所以是“另类”的。这点,与一般意义上的刻板印象有所不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