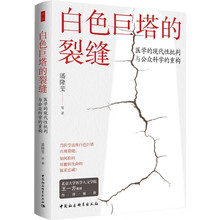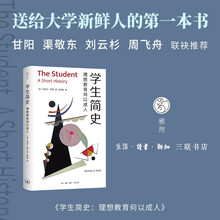1963年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黑人得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美国就不可能有安宁或平静,正义的光明的一天不到来,叛乱的旋风就将继续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马丁·路德·金号召说:“我们要抵抗,因为自由从来不靠恩赐获得。有权有势的欺压者从不会自动把自由奉献给受压者……权利和机会,必须通过一些人的牺牲和受难才能得到。”正是由于千百万人奋起抗议,要求平等和权利,黑人的人权状况才得到迅速改善。美国的妇女权利运动基本上也是这样的过程。美国的民权运动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社会的民权进步有重要启发。
在当下中国,维权抗争不断发生,抗争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扩展。就内容而言,有土地维权,还有环境维权,也有选举维权,等等,内容十分丰富。就形式而言,维权过程中的组织化程度在提升,集体行动能力在增强,政治谈判能力在提升。我个人认为,这种维权行动的兴起,既是民众权利意识提升的结果,同时,民众权利的进一步伸张,政治体制转型,也取决于民众维权抗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我认为,有了农民的公民能力巨大提升,再具体说是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维权行为的强力崛起,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有了希望。如果只有学者讲先进理念、民主制度、理想模式,而这些东西不被基层民众所接受和理解,或者说,这些所谓先进的理念、制度不能转化为基层民众对政治的理解和行动,那中国的政治今后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农民觉醒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现在看中国的政治改革现状,当然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很多,但是没有必要悲观。虽然具体的制度安排没有变,政策规定也没有变,我觉得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要变。要看到农民的进步,因为真正决定制度的进步的是农民,决定政府进步的是农民。当然,也没有必要焦急,或者总是抱怨改革步伐不快。因为只要民众的公民能力水平达不到,公民力量对于社会政治的实际作用力不够大,实质的改革进程不会理想。所以,要推动政治改革,关键是如何提升公民力量。
我个人观察,当下的中国农民正在发生飞跃性的、跨时代的变化,呈现出旧农民与新农民的根本性区别。新生代农民更加务实,更加理性,更加崇尚自由和平等。他们对政府的理解其实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上。至于“崇高理想”和“响亮口号”,他们其实并不在意。新生代农民的生活要求或者说权利主张,不论属于经济权利还是社会权利,其实都绕不开政治问题,即必须通过政治权利的落实来解决。新生代农民的成长,本身即为新公民的成长。不管在现行制度上是否被作为市民接纳,他们的要求和行为逻辑在本质上都是市民化的要求。这种市民化的要求根源于他们对于自由平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植根于天赋人权,而不是基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给他们规定了什么权利。如果他们的这种要求得不到承认,他们就会本能地抵制和反抗这种制度和政策。
我认为,在当代中国,新一代农民与他们的父辈的根本性区别,类似于法国学者孟德拉斯所说的旧农民与新农民的区别。孟德拉斯在1960、1970年代考察法国农民的新生代时指出:“人们会禁不住地确认,归根到底,这种代际冲突是一种文明冲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