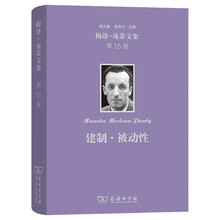但要说到在知识界的声望,施特劳斯就远远没法与伯林相比——至少在汉语知识界如此:伯林去世时,大陆和港台的知名文化思想杂志如《读书》、《万象译事》、《公共论丛》、《二十一世纪》、《当代》等等,都刊发了纪念文章。
伯林文章潇洒,在知识大众中声誉卓著,有自由主义价值捍卫者的美誉,甚至一些诗人、艺人也为之倾倒。施特劳斯从不对知识大众说话,据说是保守主义思想最深刻的教父。不过,这类“主义”卷标诱人卷入流俗、浮惑的意识形态之争,不可轻信——重要的是关注事情本身。
1958年,伯林发表了给他带来卓著声誉的“两种自由的概念”一文。没过多久,施特劳斯就在“相对主义”(1961)一文中纠弹伯林。伯林自称英国经验理性传统中人,其思想逻辑明晰有力、咄咄逼人,施特劳斯却偏偏纠弹伯林“自由”论的常识性逻辑矛盾:伯林将消极自由看作一种绝对的价值,论证却是如下宣称: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施特劳斯并没有就消极自由的观念本身说什么,仅指出伯林用来支撑消极自由概念的相对主义价值观,恰恰是一种绝对主义。既然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何以可能将消极自由作为一种绝对的政治价值来捍卫?
这一再明显不过的自相矛盾相当奇妙,也意味深长。一个自由主义者没有想到,以自由为尚的自由主义主张本身同样具有思想的专制性质。伯林看到这样的纠弹,心里不知作何感想。伯林访问芝加哥时,曾与施特劳斯促膝长谈。伯林晚年对采访记者忆述说,施特劳斯“很有学问,是一位真正的犹太教法典学者,……是谨慎、诚实而且深切关心世界的思想家”。说过这番同行客套话后,伯林马上申明,自己与施特劳斯“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本谈不拢:施特劳斯竟然还“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永恒不变的绝对价值”——超越时间、地域、民族的真理,简直是在侮辱现代哲人的智慧。伯林打心眼里不屑地把施特劳斯当老派学究,没有经过启蒙精神洗礼似的:都二十世纪了,竟然还谈什么“上帝赐予的自然法则”。
从中古到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的犹太裔思想大家代不乏人——从哈勒维、迈蒙尼德、斯宾诺莎、马克思、西美尔、列维纳斯到德里达。这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是,意味着什么呢?散居欧洲各国的犹太裔哲人在思想上完全被希腊-犹太-基督教的欧洲文化同化了,抑或恰恰相反?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不仅是政治存在问题,也是精神文化问题。所谓希腊-犹太-基督教的融贯一体,会不会是文化假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