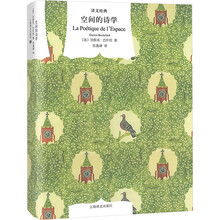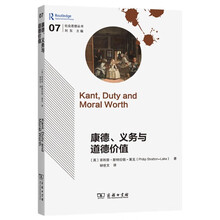因此她提出“这个历史是如何开始的”这一问题(同上,第22页),而这个问题与“女性的依赖尚未达成”的断言又是否兼容呢?如果有一个开始,那它是否必然走向事件(缔造者或者触发器),走向一个未来或者一个本质?波伏娃规定了问题的实质:不是性别的二元性引起冲突,也不是其中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绝对支配,而是男人赢在起点。
波伏娃同意两个“明显的事实”:二元性最终导致冲突;性别的二元性一上来就作为主要的二元性施压,它的原则在于产生一个不容置疑的结局,既然女性接受作为“他者”的生活。换句话说,性别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会由其中之一的决定性胜利来决定赏罚。这就是便利性所在,它们值得被特别强调,但不会超出波伏娃所提的新问题的高度。相反,它们建立了论题的基础,的确引进了对女性作为绝对他者这一形象的限定。这就是“女性作为他者的唯一事实,质疑了男性从未能够给予的所有证实,很明显,这些论据和理由是受后者的自身利益所支配的”。(同上,第22页)这些合法化的证实不仅仅是围绕着一种统治意识形态来组织的,意识形态总是我们习惯批评的对象;这些辩解并不集结为一种目标在于创造幻影的虚构,也不在于一种乐观的幻想,以取代令人消沉的现实——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并没有一个完整存在的世界,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只有被男人构建的世界。唯有一个男性统治曾经改变的公共世界,唯有一种新分配制允许平等地重新分配的公共世界。公共世界不是原初的,它可能是未来的。波伏娃有理由站在浦兰·德·拉巴尔(Poulain de la Barre)①的陪审团之列,“男人关于女人的所有书写都是可疑的”。所有的书写都有必要借用论证的风格。通过风格的恩赐,女性的依赖性已经达成,或者被证实。在这个因袭化的世界,有事件、生成性或者本质,用来论证女性的依赖性。回顾对生理学、精神分析学和唯物论的分析,波伏娃取消了这些话语的所谓胜利:“这个世界总是属于男人的,任何一个被提出的理由,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充分的。”(同上,第109页)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