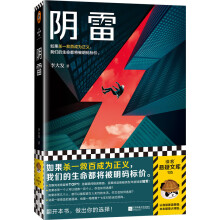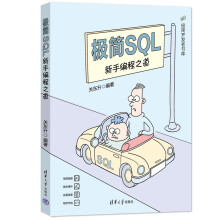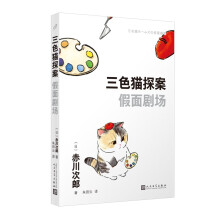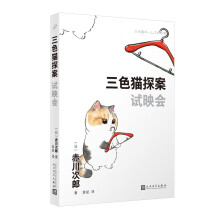比如鲁迅,他其实并不在乎自己的所谓文学家的身份和作家的职业生涯,并不认为放弃小说而去从事杂文写作是什么损失。茅盾与巴金,或许还包括郭沫若,几乎都是在一种不情愿的状态下才成为文学家的,如果他们有更加直接的机会和手段去变革社会,不见得会退而求其次在书房中开辟新战场。当然,在现代以来,所谓文学艺术,从来都是新的社会理想的内在构成部分。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韩少功这里,他的思想视野并不是文学之外的事物,而是他的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他文学叙述的不绝的动力,甚至是他的叙述策略和技术。所以,我们又看到一个孜孜不倦地追求文学形式的作家,一个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的作家,有时甚至给人以“很纯文学”或“很先锋”的感觉。他从不屑于在自己的小说中直接地流露对现实的激情,可以说,在韩少功这里,“思想的深切与格式的特别”是并重的。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少功的写作对于当代文学来说是有典范性的。他既不断地创造对当下和未来的想象,也在不断地创造着关于文学自身的想象。在他的笔下,文学的边界是不断地敞开和拓展的。尤其是到了《马桥词典》、《暗示》及之后的时期,文学是什么不再是自明的和既定的东西,而是一个不断被挑战、不断被发现和创造的场域。而在我看来,这正是当代文学之谓当代文学的本质所在。一个有出息的作家,从来都不会怀揣着所谓永恒的审美价值的幻觉去写作。所谓伟大的文学传统与成规从来不是绝对的神圣圭臬,相反,这种传统与成规恰恰正是过往的、某种特定的“当代文学”所创造出来的,它们深深地植根于历史性与地域性(民族性)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审美标准与传统的代表与象征,正因为它们当初曾经是合格的、优秀的当代文学!正由于这样,它们才被历史所肯定,抽象化为一种普遍性的标准。优秀的当代作家,从来都是在尊重这种传统的前提下对它加以挑战,从而拓展“文学性”的边界,丰富甚至修改对文学的界定。为了发现、创造新的现实,一个当代作家必须意识到文学作为制度或装置的历史性及限制性。韩少功对此具有清醒的意识,事者则是用神化的光环覆盖了真正的大众疾苦。韩少功所关注的是最普遍的人群里最凡俗的人生中蕴藏着的丰富而复杂的人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