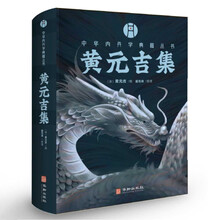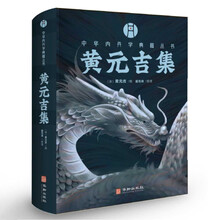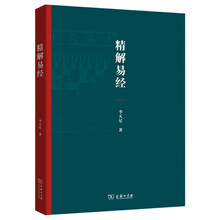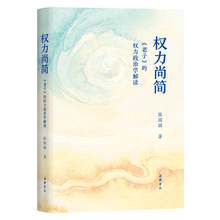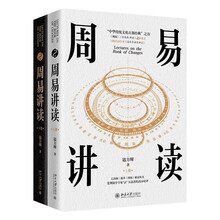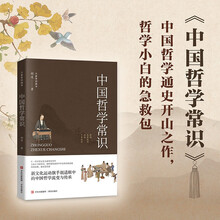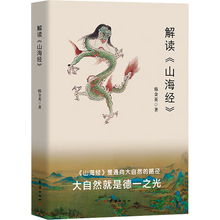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也。(《荀子·儒效》)
荀子的苛责不必引为确论,但每每以惠施与邓析为俦伍决非出于偶然。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邓析》二篇、《惠子》一篇可以想见,邓析、惠施的著述在战国末期尚流传于世,以苟子之博学和其在所撰《不苟》、《非十二子》、《儒效》等篇章中对惠施、邓析的一再评说相推度,他一定亲睹过邓、惠的遗作,而且他对邓、惠以同道视之也一定于其著述有所依据。今本《邓析子》诚然为晋人伪托,其中理致或不尽合邓析之旨,但其篇目“无厚”、“转辞”则当是原著所遗。这“无厚”或正与惠施所谓“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之“无厚”意趣略通,其“转辞”亦可比拟于庄子之“卮言”或“连犴无伤”(《庄子·天下》)之语,而与惠施所谓“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南方无穷而有穷”等“两可之说”(刘向:《邓析子叙》)之“两可”言说方式相契。然而,惠施曾如何汲取邓析学说之智思,其可能的学脉传承是否尚有中间环节,则显然因着文献的佚遗再也无从探知其究竟了。
惠施与庄周是学术史上难得一见的诤友;与荀子出于儒门而严辞非难子夏、子游、子张以至子思、孟轲构成一种有趣的对比,道术根柢处大有径庭的惠施、庄周竟可以终生为友而相晤论学。《庄子,徐无鬼》中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讲述故事的庄周是自比于那位斧艺绝伦的姓石的匠人的,这当然可看出他那恣纵不傥的生命情调,而他把惠施比作那个面对挥动的利斧“立不失容”的为“质”者,也足见被其引为论辩对手的惠施是何等沉着、从容而涵养深厚的人物。其实,庄周和惠施所以有可比之匠石与其质者关系的那份学缘,乃是因着庄周的“齐物论”与惠施的“合同异”的卓识之间有着足够大的通而不同的张力。庄周由“齐物”而倡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惠施由“毕异”的万物毕竟“毕同”而称论“天地一体”,在这“天地一体”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相较处最可见出惠、庄之学的相通而相异。这是一种独特的学缘,它砥砺了惠施“合同异”之辩的凌厉辩锋,它也激发了庄周祈于“齐物论”而“物化”以“游逍遥之虚”(《庄子·天运》)的诡异灵思。而且,重要的是,这学缘也使学术史有了一份不期然的收获,它让后来散佚殆尽的惠施之言得以在《庄子》一书的不多的辑录和记述中略存其大旨。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