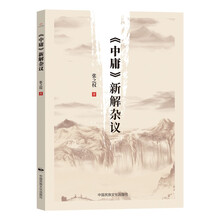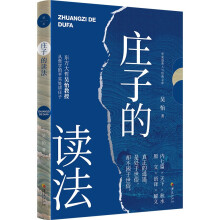事实上,道家并非对政治这一人类重要的活动视而不见、有意回 避,如同谈论天地、生死、智慧之类的话题一样,道家也把政治作为 一个话题。只是按照道家特有的风格,他们不把一般人十分看重的政 治当作什么神圣的东西,而是经常把它当作调侃的对象。庄子就曾经 说,生活中一个小偷儿去偷人家一个衣带钩是要受到惩罚的,可是那 些上层的政治人物偷得国家政权却变成了堂堂诸侯。之所以有这样 的反差,就在于小偷儿的行径是处于法律的监控之下,而法律又是 政治的一个组件,无论政治体系多么复杂精密,它总是人造的而非 自然产物。因此,本质上说,凡是将东西易主都可以算得上偷,都应 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不要忘了,法律也是人造的,唯独管不了它自 己的主人。法律的主人,当然就是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所谓诸侯。对偷儿来说,谁是国君并不重要,因为无论谁当国君都要惩罚偷儿;对国君来说,谁是国君很重要,因为如果别人做了国君那自己不是去世了便是失败 了。所以,历来取而代之的篡位者窃取的就是权力,至于能够保障权 力有效实施的制度,那都是现成的,就像对偷儿的惩罚条款一般总是 不会大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篡位者尽管是大盗巨偷,但唯其买卖 做得够大,大到连惩罚偷盗的法律执行权和执行方式一并收归己有,那当然是不用担心受到制裁的。这就是著名的“窃国者诸侯,窃钩者 诛”。庄子提出这样的观点,当然充满了讽刺,虽说很有道理,但多少 有点情绪因素在起作用。在道家的高人中,平静理智地谈论政治也是 很寻常的,老子就有不少论政之语,比如“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和大怨,必有 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以智治国,国之 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等等,姑不论我们能否接受、是否赞同,至少可以看出这些都是有思想深度的治国建言。道家喜欢寓言,《列子》这一则也是以寓言的手法戏说政治的,看上去是两拨人在斗嘴,但其中却蕴含了对政治的理解。政治究竟是 什么,这不是能够一言以蔽之的,但可以肯定政治是人造品。双方争 论的问题实际上是孰贵孰贱。邓析以支配权为贵,别人听从你,别人 为你服务,那你就是贵的。这样的人,当然就是执政者。这个观念很 有点世俗化,至今很多人还是认同的,古人称州的地方长官为“州牧”大概也是这个用意。伯丰子一方并没有正面与此观念交火,这也是辩 论术中的一个技巧,通过一个实例他们绕到了邓析的背后,反过来把 邓析套了进去。我们撇开辩论术不谈,这话中就有两个要点:一是实 例中所指齐鲁之国丰富的专门人才和缺稀的“相”究竟是什么关系,二是“执政者,乃吾之所使”究竟作何理解。先说第一个问题。用今天的话说,这涉及管理学的一些原理,专 门的人才和自然资源一样,如果调配、使用不合理,不仅不能充分发 挥其作用,有时甚至会造成不小的麻烦。这个问题在今人并不难理解,但并非所有人都能有深度感受,因为远非所有人都对管理工作有亲身 的接触。然而由此却不难想见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因此社会要求人们 对管理者必须服从,而管理者事实上也总是面临着复杂艰苦的工作。通常人们不了解这种工作的全部内涵,所以片面地艳羡为官者的威仪 与财富便成了世情常态。在道家眼里,管理确实和放牧牛羊是同—个 道理,但他们所取的并不是人比畜牲高贵这样一个意义,而是说牛羊 也是自然之物,它们有其自身的特性,能不能依据这些特性使之更快 更好地成长是做一个好牧人的关键。管理百姓,就要把百姓也视作自 然之物,总是和他们的天性相龃龉,那就不是好官了——当然,好牧 人也不是万事由着牛羊、百依百顺的意思。只有合理地把握百姓的天 性,使之顺利成长,才是无为而无不为,这才是道。另一个问题,说执政者是“吾之所使”,是受我支使的——这个我 是谁?当然,在文中是指伯丰子一班人,问题是这班人以什么身份自 居呢?一种可能,以贤者自居,道家说的贤者自然是指“有道者”。齐 鲁之国有的是好木匠,有的是好铁匠,有的是好军人,不过是精通一 门技艺。你们这样的执政者也不过是精通律法制度,所以忝居其位,充其量只是个特种工匠罢了。但是很不幸,执政者真正需要的技艺是 “道”,你们不懂,终究要向我们这些贤者讨教,这不是受我支使吗?另一种可能,以平民自居。民是自然万物之一,他们也按照大道繁衍 生息,像要求有人耕地、有人打铁一样,他们要求有人出来把他们管 理起来,以期能够更好地生活。这样看来,执政者不过都是被民众支 使的奴仆罢了。从文义来看,第二种理解或许有些偏离,而且,道家 的性格也不是动辄要说“民贵君轻”的。但无论从哪个理解看,道家 对人群中的官与民、对政治的本质都有着其独立的理解,他们断不都 是看到政治就避之唯恐不及的。而把政治也纳入“自然”的范畴,将 其平等地视为万物之一,这也正是道家思想的一种体现吧!P27-29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