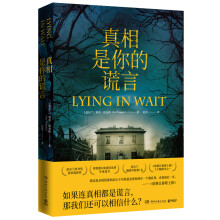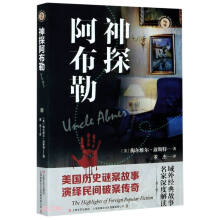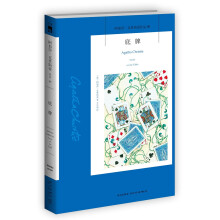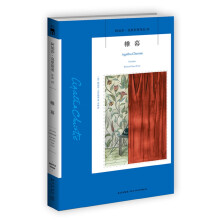梁红:从你这篇《做了一个梦》说起,我觉得你写的是女性版的《聊斋》。蒲松龄写的是穷书生的性幻想,希望拥有狐狸精一样的女人。而你写的《做了一个梦》,则是女人普遍的择偶观:儒雅温良、细心体贴、怜香惜玉的知识分子。当然,这对大多数女人来说,不过是个幻想。是怎样的契机让你动笔写这篇小说?后面的“穿越”,我第一次看到小说,就觉得是你写到后来才想到的,不是一开始就构思好的。是因为不“穿越”的话,很难突破同类的小说吗?你相信爱情吗?还是像你笔下,觉得爱情不过是一场虚空的梦想?
方格子:不知我是否可以这样回答,坦率地说,我每一个小说的最初形态都是一闪念,一闪念给了我无穷无尽的遐想。在我上班去的路上,要经过一座古老的桥,叫“恩波桥”,是富阳保存完好的古建筑之一吧,它曾经有个美丽的名字,叫“恩波夜雨”。桥旁边有一排树,香樟树,初夏的香樟树好像是要落叶的,满街飘荡着被风吹落的树叶,整个小镇都弥漫着树叶的香味。有一次我经过一个擦鞋的摊,一个短发女子正弯腰为一个中年男子擦鞋,阳光晴好,日子多么美丽。那样一个场景忽然之间让我感动,也就是我一闪念间的事,我忽然想,就在那一刻,当一片香樟树叶掉落到女子的肩膀,女子看了看树叶,又看了看男子,他们相视一笑,那是爱情吧。那是我忽然想要写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的开端。
事实上,我是个爱情不信任者,我觉得所有的爱情都只是一瞬间的感觉,是一个人内心脆弱或者情感迷乱时忽然出现的对异性的依恋,至于后来的追求和念念不舍,在我的理解里,都是因为不想否定初衷,想追问“人生若只如初见”那样的清丽。
这个小说,是我搁置时间比较久的一个,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写绝了自己的路,再也找不到一条出路了,无论怎么写都是在重复,我不愿意那样。没有人强迫我写作,那就不写吧。到一万字左右的时候,我全盘否定了它,我觉得这个小说和我以往的任何一个没有出路的爱情小说一样,不可能突围。 是一个梦救了我,是一个梦救了我的小说,确切地说,是一个梦,为我在前面劈出一条路来,我看到了梦里的人和事。既然现实中没有爱情,那么,就让所有经历过的伤感成为一个梦。不相信爱情,却又愿意津津乐道于爱情的辩白,我确信,爱隋是有期限的,像一张存单,看起来任何时候都可以去取,但是,它陈旧了,不新鲜了,就算有再多的利息,我也不会在乎了。我这么说,你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被爱情点了伤穴的人,因为得不到,还不如说没有。呵呵。
梁红:我看完了你的中短篇小说集《锦衣玉食的生活》,这本小说集,大部分写的是市井女子的生活。这些生活是片段式的,一个个细碎的碎片,分寸感很强,描摹到位。读你的小说,像看水墨画,留白的地方多,所有痕迹都是淡淡的,不那么着力强调,墨迹有水洒上去时,会氤氲开,和背景融为一体,分不清是水还是眼泪。你的叙述冷静,不动声色,底下却是暗流汹涌。初看很平淡,细看却有让人回味的地方。这种空白,没有说透的话,恰好形成了小说内在的张力。你写小说,参考了中国写意山水的笔法吗?形成这种风格,你酝酿了多长时间?或者问你一个大众化的话题:哪些作家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方格子:那是我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我很珍惜。其实,回答问题是我最最惊惧的。你说到的“参考了中国写意山水的笔法吗”,说参考,那会让我觉得是鄙薄了那些我喜欢的天然之笔。杭州有位画家叫何加林,很厉害,我比较喜欢他的山水画,说不出原因,就是喜欢吧。我拒绝承认“参考”。我喜欢乱翻书,有时候去图书馆,翻着翻着就借一叠回来,坐下来,翻呀翻,服饰、健康食谱、军事,有时候还会借低幼漫画书来看,绿色是绿色,红色是红色,夸张的漫画,觉得真好看。
我的阅读量很小,这是我尤为惭愧的一个方面。有那么几年,我漂泊在外,一个朋友听我虚荣心膨胀之时说出张爱玲这个名字,就搬来了那个书店里全部的张爱玲作品,在那漂泊的三年时间里,事实上是张爱玲在温暖着我。也因此,她的作品让我欲罢不能,一度成为我精神的支柱。这样说来,我的写作怎么可能不受她的影响呢?
再要说的是,在我的精神领域里,还有另外一位作家影响着我的创作,我把他看做我面前的一座山峰,我仰慕。我这里说的影响创作不是文本的创作,而是一种坚持和对于纯粹精神的向往,他(你看你看,又出现了一个“他”,可见小说里的“他”事实上都是可疑的)总鼓励我:“你要咬紧牙关好好写作。”“你不要放弃。”“写是实,其他都为虚。”等等这些,在近些年包括现在惘然的日子里,成为我精神小屋的一微烛光,我会觉得写作的强大,我会深刻体会到正面力量给予我的支撑。由此,我常常自省,试图从纷繁之中拔足而起。
梁红:《锦衣玉食的生活》可以说是你的成名作。这个标题,一不小心会让人误解,以为是写“上流社会”,事实恰恰相反。“双下岗”(失婚兼失业)的女主人公艾芸,用一种荒诞的方式寄托来生的梦想,她如此执著于来生的“锦衣玉食”,这种对今生的绝望,读来令人唏嘘。而最后,她却车祸身亡,千方百计穿好的锦缎华服并没有陪伴她,还是由灰扑扑的衣裳陪她最后一程。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荒诞的,在“生活真实”上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它其实是提炼了的比生活更真实、更残酷的“真实”,这种真实感让人不忍卒读。这个小说,我认为奠定了你在当代女作家中的地位,写市井女子,你有不可替代的个人风格。你自己认为呢?这个小说有故事原型吗?
方格子:我几乎没有重新回头去读自己那些已经发表的小说的习惯,但这个小说例外。我在最近一次的阅读中,忽然对艾芸这个女人抱有另外一种情感,真的,也许对于积极世界来说不可取,我想,艾芸为什么不和她的好友麻莱发英一样,每日搓几板麻将,说说家长里短呢?快乐的形式多种多样的呀。后来想想,似乎是工艺厂的那一点残存的艺术气质害了她,使她树立了崇高的理想,“人要是没有理想,就像种在西堤路上的马褂木,马褂木好歹还能派上用场,人没有了意志就废了”,也许就是那一点对世界的不妥协害了艾芸。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