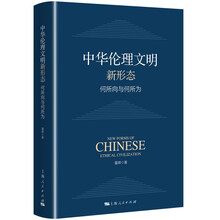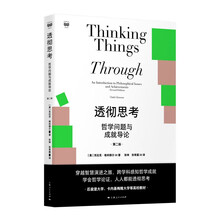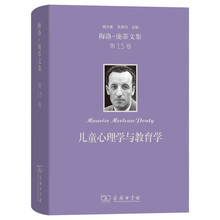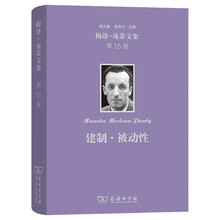这种根据“本来”并不从属于自我的领域来限定“本来”从属于自我的领域的否定性的做法,至少包含着以下五个主要困难。
(一)在这种作为经验的现象世界的一种意向性构成成分而存在的,经过先验还原的领域之中,人们必须既能够识别“本来”并不从属于自我的领域,又能够识别这种领域本身,这样才能从它出发进行抽象。就我所能够理解的范围而言,这种表述也是与包含在《笛卡尔式的沉思》的文献之中的精确措辞相一致的。包括来自《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书的几段话在内的几份文献,都提到了某种与“本来”并不从属于自我的领域有关的“预先构造的基质”(Unterstufe)。对这种基质的预先构造过程究竟是哪一种构造过程呢?它又是如何发生的?这种基质究竟是什么?如果从对这种基质的分析开始,就必定无法彻底阐明“本来”并不从属于自我的领域吗?不仅如此,这种“本来”并不从属于自我的领域——我要想揭示原初的超越,就必须由之出发进行抽象的这种非主我——究竟是如何具体展示其自身的呢?
(二)应当由之出发进行抽象的这种关于“‘本来’并不从属于自我的领域”的概念,也是非常不确定的。甚至把各种动物和人们都当作“像自我那样”活生生的存在而等同起来的做法,也是非常不可靠的。此外,谁才是“自我一主体”意义上的“其他他人”呢?而且,他们所具有的、有可能为某种关于其他他人之经验的构造性理论发挥某种先验线索作用的、具有意向对象性—实体性(noematic-ontic)的给定方式是什么?他们都是其他的个人性自我吗?或者说,他们都是作为各种习惯的基质而“发挥核心作用的”其他自我吗?抑或,他们都是以其完全具体的状态存在的其他自我?就“每一个人”这个相关概念而言,也出现了同样含糊不清的情况。显然,每一个人就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像自我那样的(ich-artig)存在;然后,在另一个时刻,它就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而在第三个时刻——至少就各种文化谓项而言——它又有可能是“相应的文化共同体的任何一个成员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