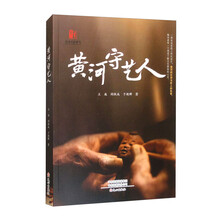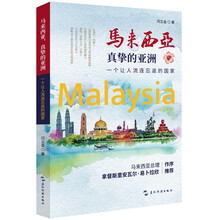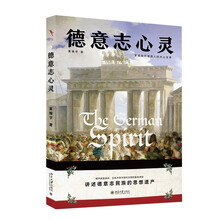2.正考父、孔子与诗篇的编制
《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女,执事有恪。”
其中的记载很明确,正考父是“校…‘商之名颂”,但《史记》却称之为“作”:
《史记,宋微子世家》: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
这两则记载看似矛盾。“校”与“作”在后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文献措辞的不同使人们很自然的以今例占,因而认为二者之中有一个一定是错的。事实上,如果参照“赋”的“造篇一诵古”模式,就会意识到,当时的“校”与“作”并不像后代区分得那么严格,不仅实际中往往会混同在一起,而且人们的相关观念也是模糊的,有关记载由于角度不同自然会形成不同的说法。客观上,当时个人独立的文学原创模式还没有确立,作品不仅往往作者不明,而且在流传中还在不断变化、形成,作者的系属也会因此比较灵活;正考父对《商颂》的校理,是《商颂》流传过程中熏要而知名的事件,这就很容易形成正考父“作”《商颂》的说法,而这个“作”在当时不可能是后代意义上的文学原创。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