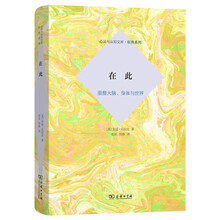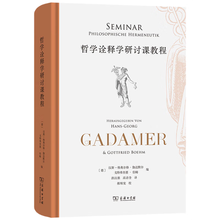6.3.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与《春秋》获麟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人对于一生道路的回顾。在什么时候一个人可以回顾一生?在一生成为一生的时候。
左氏之《春秋》经文止鲁哀公十六年,传曰“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羊和谷梁止十四年西狩获麟。为什么在这里停止?公羊十四年传曰:
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麇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
子路之死在获麟之后,为什么这里的书法却要提到获麟前面来说?是因为在看到麟的瞬间,这个人的一生便成为一生?在看到麟的瞬间,一生的年龄才突然相互临界地排列起来,际会起来,成为一生的年龄?由此,岁月的编年,春秋的代序,方才犹如鳞次栉比一般各安其位?而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七十,除了是与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临界并列的年龄区段之外,是否首先是因获麟而突然际会而成的这整个七十多年作为一生的整体时间?然后,只有从这个一生整体时间意义上的七十出发,回首生命的道路,际会年龄的临界、鳞次与比邻,才有区段年龄意义上的十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和七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本就是七十之年同时作为际会一生的整体年龄和临界区段的年龄这两重年龄属性自身所涵有的位置特点了:“从心所欲”说的是这个年龄位置的际会性,“不逾矩”说的是这个年龄位置的临界性。
这个年龄位置的两重性是由麟之位置的错位带出来的。麟的到来,不合时宜,也不在其位,因而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到来:“何以书?记异也。”这个异之为异,一方面表现在空间上的错位:“何异尔?非中国之兽也。”一方面表现为时间上的错位:“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时空皆错位,所以“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
但这还仅仅是公羊传的一家之言。麟之为异也许尤其在于:无论关于麟的空间位置,还是关于麟的时间位置,以及相应地,麟何为而来,麟之来是兆亡的灾异还是祥瑞的灵异,又如果是祥瑞,那么是为汉兴之瑞还是因春秋文成而为孔子瑞,甚至麟来是在作春秋之前、获麟而感作春秋,还是作春秋在前、文成而感麟至,这些都还处在众说纷纭的不确定之中。在《春秋》三传、今古文两家源远流长的学术传承史、辩驳史上,在这些问题上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有时候甚至在同一阵营之中还略有差异。
概而言之,左氏以为麟生于火(南),游于中土,为中央轩辕大角兽。服虔以为中央土属信,信(土)为礼(火)之子,孔子作春秋是修礼,母修则子至,故麟来为孔子修礼之瑞。这是把春秋的主旨理解为维护周礼,义在继往。公羊以为麟木精,东方仁兽,赤目火候。何休解诂以麟来为周亡之异而汉兴之瑞,犹木生火之义也,经止于春,其义同此。这是把《春秋》的主旨理解为垂法后世,志在开来。陈钦以麟为西方毛虫,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而西方兑,兑为口,故麟来为孔子立言之瑞。许慎诉诸《礼运》四灵,以麟配中央,又据吉凶不并、瑞灾不兼的原则以麟来既为周亡之异,就不可同为孔子之瑞。郑玄则诉诸《尚书》洪范五事以驳许,以为孔子春秋立言垂法,天应以金兽性仁之瑞,兴者为瑞,亡者为灾,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说为密。郑说实际上是综合了麟来为孔子立言垂法之瑞、为周亡之异和为汉兴之瑞这三种说法,而摒除了修母致子(其实质在于以《春秋》为修周礼之作)这一种说法。皮锡瑞以为郑玄的综合,可以疏通公羊与左氏诸家之说的不同。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