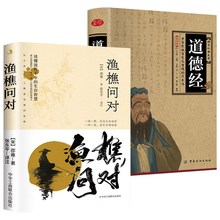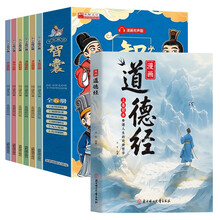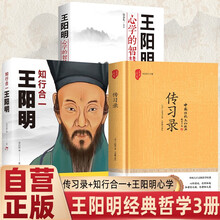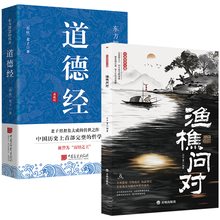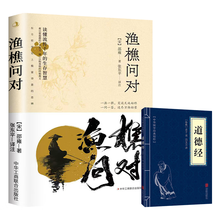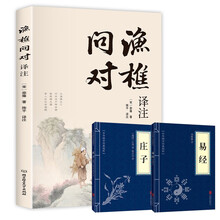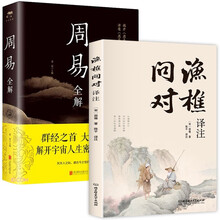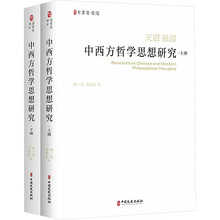第一章 前面的话<br> 一、我为什么这么恶<br> 《韩非子》中没有专门论述人性的章节,但处处闪现了对人性的理解,韩非始终没有对人性进行主观的褒贬,他用一种近乎冰冷的语气在谈论人性如何如何,人们应该如之何如之何。可见韩非的头脑中并没有人性本善或者人性本恶的区别,他只是在就事论事。<br> 人性本来就是这样的,趋利避害,可能成为建设者,也可能成为破坏者。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不会无偿做好事,也不会不计后果地做坏事。韩非并不关心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只关心什么是有用的。正因为有此不同,有些人便将“性恶论”的标签贴在了韩非的身上。其实韩非主张既非性恶,也非性善,他已经超越人性的善恶,关注的是君主怎样才能更强大的问题。尼采在《超善恶》中要阐述的意思,有两位古人已经模糊地感觉到了,一个是我们的韩非,另一个是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br> 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儒家对人性的定位已经深入人心。孔子在《论语》中有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讲的是仁义,小人讲的是利益。按照孔子的说法,韩非思想应该归入小人一类,是恶的价值观。我们姑且采用儒家的说法,暂将韩非思想定义为“恶”。<br> 现代读者不禁要问,韩非为什么要推出这种“恶”的学说呢?要知道任何学说都是时代的产物,黑格尔说过哲学这东西就是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临近傍晚的时候才会哇的一声从枝头起飞。当战国这段大争之世快要结束的时候,韩非哇的一声,于是便有了惊世骇俗的《韩非子》。与《韩非子》堪称姊妹篇的《君主论》与《韩非子》有异曲同工之妙。<br> 《韩非子》虽然像2002年的第一场雪一样来得有那么点晚,但还是赶上了秦始皇的二路汽车。秦以后,法家的作用没有减小,但地位却下降了,曾经的老对头儒家被捧上了高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法家太务实了、太深刻了、太有力了,这些长处反过来也是短处。有些领域并不适合法家思想,比如教育、宣传、祭祀、文化等。总而言之,一切和国家形象、精神文明建设有关的领域都不太适合法家,但在典章制度、人事安排等方面,法家思想依然起主导作用。<br> 儒家与法家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两者的界限总是模糊不清,而且相互渗透,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重大改革时期,儒家总是希望德才兼备的能人扭转历史,而法家则试图通过改变制度取得成效。<br> 儒法两家瓜分了官方市场,在民间市场中又有了道家的参与。道家对中国人的影响主要是在社会交往及人情世故方面,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很有点打太极的味道。由这些思想形成的社会规则和潜规则既不明晰也不确定,看似不着边际,其实处处存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既能将小人捧成明星,也能将英雄拉下马来,我们总是用一生来学习这些东西。<br> 小时候我们受到的教育是人性是美好的、社会是充满爱的、位居高位者都是品德高尚的君子,可是当我们走进社会才发现真实的世界并不像教科书上那般美好,于是乎怀疑产生了,人性是善还是恶?<br> 如果我们拿这个问题采访一名罗马人,一定会让他满头雾水。罗马人头脑中没有人性善恶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人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尽管在我们看来罗马人本性邪恶、贪婪、好斗。孔夫子教导我们说君子要远庖厨,可是在罗马连最文雅的人都乐意观看角斗士捉对厮杀的血腥场面。<br> 人性善恶虽然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但却很难说清。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有的人做而不说,有的人说而不做,当然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怎么说就怎么做,他们要么是高不可攀的圣人,要么就是招人喜欢的性情英雄——曹操的那篇《让县自明本志令》是一种反传统的写法,没有善的虚饰,恶得率真可爱。最苦恼的莫过于那些离开儒家书房,刚刚走进法家竞技场的青年朋友,难免会有被欺骗的感觉。中国古代许多“学而优则仕”的官员都有过这种奇妙的人生经历。<br> 这里有自己改编的小诗几句献给大家: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生气,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看一看《韩非子》,你就会心明眼亮、茅塞顿开。儒家的存在是政治的需要,代表了人们的美好愿望,而法家则揭示了更多的客观实在。<br> 抽象地、形而上地讨论人性的善恶或许没有意义。这本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解答,一个人能够证明人性多么善,另一个人就能证明出人性多么恶。虽然人们对人性善恶存有争论,但对人性可塑却少有质疑。所以相比于旧《三字经》开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觉得新《三字经》开头“人之初,如玉璞。性与情,俱可塑”更贴切,前者的语气先验而独断。人性的可塑性在不同学术大师的作品中有不同的反映。<br> 韩非对人性的认识是时代的产物,就像勒·庞对群体心理的认识也是时代的产物一样。战国时期,韩非看到了人们毫无顾忌地追逐利益,才得出人性趋利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套富国强兵尊君的理论体系。<br> 像任何一部伟大著作一样,《韩非子》反映了时代,超出于时代,照亮了后代。如果没有战国,就不会有韩非这样的政治理论家,同样如果没有民国,就不会有鲁迅这样的战斗文艺家。战国是一个精彩纷呈、独具魅力的时代,不然怎么会产生《韩非子》这朵奇葩?英雄需要土壤,学术同样需要土壤。关于战国,我曾经用不小的篇幅去叙述,但仍感觉只触及不及万分之一的精彩。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