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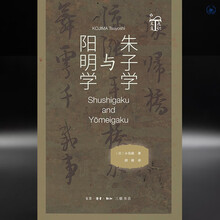




《西学中的夜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而言,是“唯一的”、“最好的”,还是“独立互补的”?一百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未变?还是起了变化?起了怎样的变化?变到什么程度?今天是否到了有以明断的时候?西学中的夜行,在西学中走向起点的夜行,夜行到头了……我们必须真正回到中国文化类型的源头处,即“儒法表里,道一贯之”的“道”,即“道法自然、出神入化”的“道”,才可能有真切的言辞。《西学中的夜行》整个都是为它准备着的。
“第二次启蒙”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思想解放”后夹在萨特、弗洛伊德之中登场的尼采。
中国的“思想革命”如同历代的“农民战争”,发生在前人身上的那些思想累积并没有进人有序地增长过程,如果不是放一把火烧得精光的话,后来者几乎总是要再从头开始经历一番,如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几乎就是新一轮的重复。
尼采仍然是怀疑与诅咒的大师,而且,与其说它是“拆毁”的力量,不如说是“宣泄”和“呕吐”的工具。同第一次启蒙中的尼采相比,这一次尼采更像个酒神节上的“诗人哲学家”。所以流行的尼采“面具”只能是:
a尼采伸张“个人”的生存意志,强调现世的生命快乐,反对用任何形式的来世超世及其权威代表扼杀个人现世的快乐要求,痛苦属于无责任能力的人;
b神的或形而上学的真理不过是建筑在流沙上的“牌楼”与“偶像”,只有充满创造精神的艺术才是长久的快乐源泉;
c人们戴惯了真理与道德的假面以至把自欺当作常态;人之所以是真理的奴仆,因为他事实上首先成为了别人的奴仆;绝大多数人如此。这很正常,只有那些创造真理的少数人才是真理的主人因而也是真理奴仆的主人,他们是拥有“重估一切价值”之“权力意志”的“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