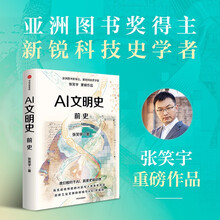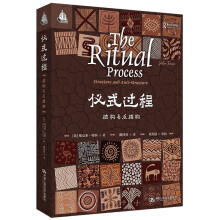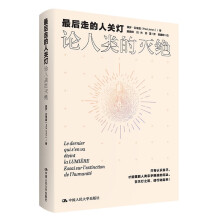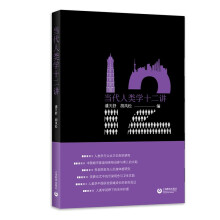19世纪进化论者力图以简约归纳的科学手段,对庞杂无序的文化和社会世界进行系统和客观的考察和研究。这种做法由于无法合理解释历史上发生的社会退化和文化消失的现象,从一开始就遭到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不同程度的质疑和唾弃。此后,人类学界“文化相对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学派(见下文专述)的出现,其实就已经否定了社会进化论的预设前提和学理价值。然而在20世纪,对于某些出于维护本身利益集团主导地位的政治需要,力图通过总结人类文化和社会演化规律来实现话语霸权的罗斯托和亨廷顿来说,社会进化论的理论假设和研究路径仍然具有无穷的吸引力。
一如19世纪的社会进化论,以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论”为标志的现代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目的论。二者都采用了循环论证的方式,都无法从实证的角度来回答究竟是现代化导致或者有助于发展,还是源自发展,或者说发展和现代化可能就是相同的过程。当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现代化理论,其始作俑者试图以文化价值观的术语来掩盖资本扩张和强权争夺的事实真相的用意,可谓一目了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三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障碍恐怕还是与殖民遗产脱不了干系的依存性问题。同样,如果脱离冷战这一极为重要的国际政治背景,光从以儒家伦理的人文魅力和精神价值来解释二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也未免贻笑大方。
20世纪新进化论和文化唯物论的学术影响虽然有限,但却给我们带来一种理性的发展观和与之匹配的科学的文化观。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