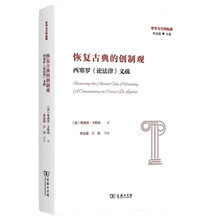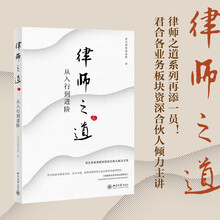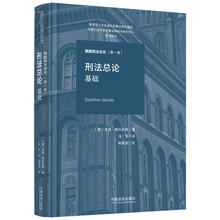与格老秀斯和霍布斯一样,普芬道夫认为由宗教分歧所导致的战争是不可调和的。因此,一种能够让所有欧洲人同意新政治秩序并能带来和平的新道德,应当独立于导致分裂的多元化宗教信条,并允许相互竞争的宗教信念和实践在道德框架下并存。这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从任何人都无法用理性质疑的两个前提中推导出一系列普遍的正义原则:一个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科学性重构状态,即“自然状态”;另一个是可进行经验性验证的状态,即自爱或自保(Seidler,1990)。前者可以使自然法摆脱对既存法典研究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出发点(公意)的依赖,从而可以摆脱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和皮埃尔·沙朗(Pierre Charron,1541-1603)的相对主义指责。后者则提供了一种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善(自我保存)——尽管人们对更高一级的善的秩序意见不一——从而可以避免将自然法的渊源和任何特定的宗教联系起来(Zurbuchen,1986)。
普芬道夫和巴比拉克洞悉到了格老秀斯理论中的这两个前提,因而指认他为新的自然法学派之鼻祖。塔克(Tuck)和塞德勒(Seidler)强调了格老秀斯和普芬道夫的这两个共同点。不过他们之间的差异仍是不容否认的。格老秀斯将其理论奠基在斯多葛式前提之上:人具有为自身利益而热爱社会的内在性情。霍布斯在《论公民》中开宗明义地驳斥了这一前提(把它转化成为“间接自爱”),并以此为起点构建了新型的政治科学。普芬道夫也否认人对政治社会的这种目的论性情的存在(但他没有遵循霍布斯的选择)。普芬道夫哲学的这一特征——与此相伴的还有:他的与格老秀斯道德实在论相对的道德强加论;他把自然法限定在保存(preservation)上;他把自然法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使得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路德教派批评者们对其正统性地位争执不休。他们否认他和格老秀斯的亲缘性,将其称为霍布斯的追随者和无神论者。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