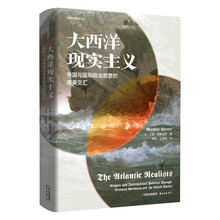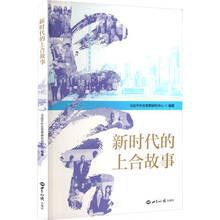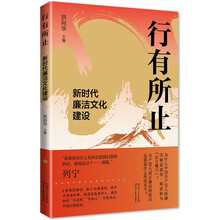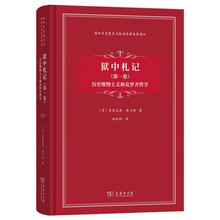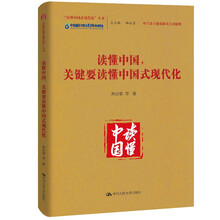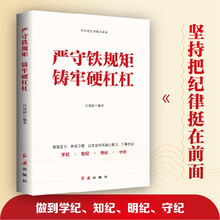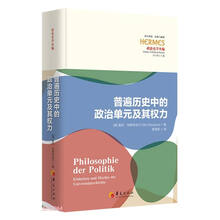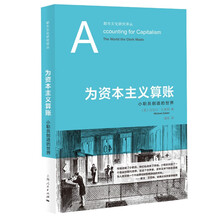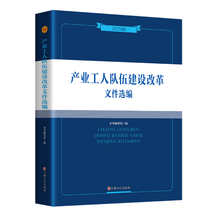第一章 政治与政治学
揭开政治的神秘面纱
进入政治学领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政治”。这一问题看起来简单,但要很好地回答,并非易事。事实上,寻求一个确凿的关于政治的定义,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许多政治学教科书开篇先给政治下一个标准的定义,试图在此基础上,阐明一套逻辑一致、自成体系的政治学基本原理,这种做法往往是徒劳,甚至还会带来误导。因为至今寻找政治学的基本原理还是极其困难的,我们所接触的政治理论、政治学说,反映的不过是人们对政治问题的多种思考之中的一种。至于什么是政治问题,还是让我们从政治现象谈起。
人类以词语来描述特定的现象,因此,理解一个词语的关键是要搞清楚我们使用该词时指的是何种现象。这就是说,当我们用“政治”一词时到底指何种现象。而各个时代、各个文化中的人们,往往对“政治”一词的理解又有所差别。既然这样,那么我们大可不必苛求于找到一条判断政治现象的唯一标准。重要的是从对话的情境中去理解人们说“政治”二字时指的是什么。一般来说,人们在使用政治一词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倾向。
政治领域:游移不定的边界
广义的政治概念,所指的包括人们共同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这些重大问题是公事而不是私事,涉及的是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团体,而不是单个的个人。这样,“公”与“私”的区分可以看做讨论政治现象的前提。在国家形成以后,政治往往与国家这一公共权威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可以说国家大事就是政治。例如,国家领导人的换届、政权的更替、新政策的实施、两国元首互访等,显然是政治问题;而家庭琐事、爱情与婚姻、个人求职、企业管理等,显然不在常识所认为的政治问题范围之内。不过,政治的边界有时十分模糊,某一其他领域的问题,在一定条件下会上升为政治问题,或被当成政治问题来处理。例如,足球赛本是体育活动,但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两个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不友好国家之间的足球赛,就可能具有政治性质,成为政治事件。
西方文化里“狭义”的政治
狭义的政治概念,特指民主政治。所谓民主,就最基本的含义而言,可理解为公民参政议政。尽管政治实践与政治思考在各个文明中都存在着,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只是在西方文明中产生。具体说来,是古希腊人首创了这门学科。古希腊人的城邦民主实践,使狭义的政治一词从最初起就有了特定的民主内涵。这样,“政治”作为一种处理公共问题的方式,与“独断”形成了截然的对比。政治意味着人们走到一起,相互交流,各抒己见,从而进行决策;这样,政治的过程,也就是一种人们就公共问题相互谈判、协商直至达成妥协的过程。所以西方的政治学家会告诉你:政治生活中没有专制者的位置。按照这一理解,中国古代的帝王统治下的帝国,其实没有政治生活,因为在这一结构中,帝王与百姓的身份是不平等的,专制君主可以不必求得百姓的同意而作出决定,甚至可以随时剥夺个人的财产,乃至消灭人的生命。所以,中国古代可以说是有“治”而无“政”,有官僚统治而无公民政治。
当政治被理解为“权术”
就感情色彩而论,人们使用“政治”一词,也常有褒贬之区别。尽管中国儒家文化以“积极入仕”来教育读书人,人们也对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显亲扬名的人刮目相看。但是,政治一词有时也在贬义的场合中使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果你的朋友提醒你,某人是政治动物,是搞政治的,你要当心点!那么这位朋友并不是在赞扬此人,而是说这个人精于权术,以搞关系、拉帮派、玩阴谋为能事。汉语中的“政客”就是专用来指这样的一类人。事实上,把政治理解为权术的运用,政治领域成了藏垢纳污之所,成了政客们无耻的争权夺利的场所,倒也体现了一种类型的政治现象。人们也常常说: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天下乌鸦一般黑;东山老虎吃人,两山老虎也有利齿;西瓜滚到京城里,只有芝麻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些俗语中反映出的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活动的许多典型现象,从中也可以看到人们对现实政治的批判。
“内圣外王”:传统中国的政治理想
中国古代没有西方那样系统的政治学理论,但是政治思想却十分丰富。由孔子、孟子所开启的传统儒家的学说,既是关于做人的学问,也是关于“为政”的学问。儒家传统把做人与为政结合起来,把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儒家教育培养读书人,同时也就是培养官员,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使得读书人常感壮志在胸而时刻准备应皇帝的召唤,尤其在科举制兴起后,读书与做官更是紧密结合。北宋宰相赵普说他自己凭借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儒家经典所包含的政治学智慧。中国古人讲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从“格物”到“齐家”,都局限于私人领域,但“治国、平天下”,则是政治问题。曾经有一个大学生辩论会,辩题正方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反方是“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不管正反两方如何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但“扫一屋”与“扫天下”的区别,所体现的恰恰是家庭私人领域与公共政治领域的分野。中国古代文人大多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志向。“学而优则仕”,体现着中国古代文人随时准备成为一名政治人,“扫天下”被看做是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标。
不过,中国古代人的政治热情并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的理念,民主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中国古代的政治理念,多少都与忠、孝、节、义连在一起,“民本”思想大胆提出“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古代民本的前提仍是皇权专制,与民主仍不可同日而语。对古代士人来说,往往忠于国家等同于忠于皇帝,由此不免造成人格的扭曲。当然,也有坚持真理和道义而逆龙鳞、批圣听的死谏者。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当代中国的政治教育当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同时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使命,大力普及公民意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而这里也涉及到政治主体的根本转变,这就是从“臣民”转变为“公民”。
政治人:从臣民到公民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臣民与公民的区别,体现着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区分。中国古代关于“民”的概念,总是与“君”、“王”相对而言。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的政治理想,简单说来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就是说,做君主的要像君主,做大臣的要像大臣,做父亲的要像父亲,做儿子的要像儿子。怎么才叫像呢?照孔子的意思,其实就是君臣有别,长幼有序,言行举止合乎礼法。从根本上来说,儒家政治维护父权,维护君权,坚决反对僭越。而这一理想,落实到现实生活的礼仪中,从臣对君、民对官的跪拜礼中便可以看出来。从理论上讲,中国古代君王确实掌握绝对的权力,君王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受法的限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伴君如伴虎”等俗语,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君臣关系的紧张。
而公民则体现了一种平等的政治身份,这种身份受到法律的保护。只有在民主社会,政治主体才是公民。公民享有权利,同时承担公共义务。公民概念在中国是现代概念,体现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在西方则是另一种情况。古希腊政治就是一种公民政治。不过,在西方,古代公民与现代公民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古代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他们要亲自参加决议、管理、审判等活动,要自备武器随时准备战斗,公民为城邦而生,城邦也因公民而具有活力。而现代公民则大多通过间接的方式影响政治,人们甚至可以安于一己私域,做一个政治冷漠的“消极公民”。在现代社会,政治领袖虽然在事实上拥有独特的影响力,但其法律身份与普通人士是一致的,无论领导者还是被领导者,他们首先都是一国的公民。
……
展开